
清晨的雾还没散透时,我踩着田埂往山里去。田埂上的枯草沾了夜霜,指尖一碰就簌簌落,霜粒凉得沁进指缝,却没冻着——刚收割完的稻茬还留着点日晒的余温,混着泥土的湿意,把风里的稻谷香烘得暖融融的。偶尔有没拾净的稻穗躺在埂边,黄澄澄的颗粒裹着细糠,捏在手里能搓出细碎的响。
走到山脚下,稻谷香便淡了,换成松针的清苦,混着野菊的甜。路边的野菊开得细碎,白的、黄的,躲在茅草丛里,花瓣上沾着晨露,风一吹就滚下来,滴在鞋面洇出小湿斑。蹲下来细嗅,那甜不是浓腻的蜜甜,是清冽的、带着点土气的甜,像刚剥开的生栗子,浅淡却勾人。
顺着石阶往上走,山就彻底被秋染透了。近山的坡上,枫树把枝桠撑得满满当当,叶子红得不是灼眼的艳,是被秋阳烘了半旬的蜜——有的叶尖带点橙黄,像被夕阳吻过;有的边缘卷着,像被谁揉过又轻轻展开;还有的叶脉里藏着没化的霜粒,阳光从叶缝漏下来,霜粒就亮晶晶的,像撒了把碎钻。风过时,满树红叶便晃起来,簌簌地落,有的飘在石阶上,有的粘在我的袖口,摸上去软乎乎的,还带着点霜的凉。
再往上,几株老银杏站在石崖边。树干皲裂着,爬满深绿的青苔,有的树缝里藏着小蚂蚁,背着比身子还大的虫尸,慢悠悠地往巢里挪。银杏叶落得满地都是,铺成层厚软的碎金,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混着叶底虫儿的“唧唧”声——是只黑褐色的小虫,腿细细的,被脚步声惊得往石缝里钻,慌慌张张间还掉了点细屑,转眼就没了影。只有松和竹沉得住气,墨绿的松针攒成簇,霜挂在上面像小珍珠,风一吹就簌簌掉在脖子里,凉得人缩一下;青碧的竹竿从石缝里钻出来,有的竹梢弯着,挂着几片干枯的竹叶,风过时竹竿轻轻晃,影子投在地上,像流动的淡墨画。
山坳里藏着条溪沟,绕着石阶弯弯曲曲地走。水比夏天浅了许多,露出大半的卵石,卵石上裹着层薄霜,阳光照下来,霜就慢慢化了,变成小水珠顺着石缝渗下去,留下浅浅的湿痕。溪水“叮咚”响,清得能看见溪底的小杂鱼,银闪闪的,顺着水流游,一碰到人影就“嗖”地钻到石缝里,只留个尾巴尖在外面晃。偶有几片枫叶飘进溪里,有的被卵石挡住,停一会儿又被水流推着走,叶面上的水珠像碎钻,还有几只小虾米趴在枫叶下面,爪子扒着叶脉,像搭着免费的船往下游去。溪边的石凳是青石板做的,凳角沾着点干枯的茅草,旁边还丢着个铜烟袋锅,有点氧化的绿锈,袋锅里还留着点烟末,闻着有淡淡的焦香——该是前几日樵夫歇脚时落下的。
快到山顶时,风忽然软了些,没了山腰的凉意,裹着点阳光的暖。抬头看,雾已经散了,天是淡蓝的,飘着几缕薄云。回头望,山下的稻田铺成一片浅黄,几株白鹭站在田埂上,长腿细细的,偶尔啄一下地里的虫;远处的村庄里,几户人家的烟囱飘出细烟,被风扯成丝,慢悠悠地缠在山腰的枫树上,像给山系了条白丝带。
山顶的石亭是旧的,木柱子上刻着模糊的字,该是多年前游人留下的。亭子里有只灰雀,羽毛灰扑扑的,肚子沾着点白,正蹦跳着啄石缝里的草籽。见了我,它也不躲,只是歪着脑袋看,黑溜溜的眼睛转来转去。我从兜里摸出颗干枣,轻轻丢过去,它先是往后跳了一下,又凑过来,用尖嘴啄了啄,确认没危险,便叼着枣儿,扑棱着翅膀钻进旁边的松枝里,还探出头看了我一眼,才带着枣儿消失在叶丛中。
日头偏西时往回走,怀里揣着几片捡来的枫叶,被体温烘得有点软。风从背后追过来,把头发吹得乱乱的,却不觉得冷——风里裹着山下人家做饭的香味,是柴火饭的暖香,偶尔还能听到几声狗叫,慢悠悠的,像跟着风走。路上的银杏叶又落了些,铺得更厚,走上去像踩在棉絮上;松针落在石阶上,偶尔硌一下鞋底,却不疼,只觉得痒。快到山脚下时,回头望了眼,夕阳把山顶的石亭染成了橘红,满坡的枫叶也浸在霞光里,像燃着的火,暖得人心里也软软的。
原来深秋的山,不是冷寂的,是藏着暖的——藏在枫叶的红里,藏在银杏的金里,藏在溪水的叮咚里,也藏在风里那点稻谷香、松针苦、野菊甜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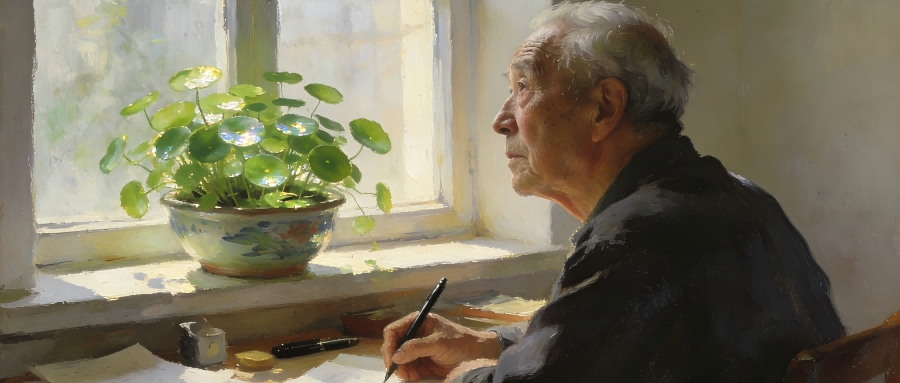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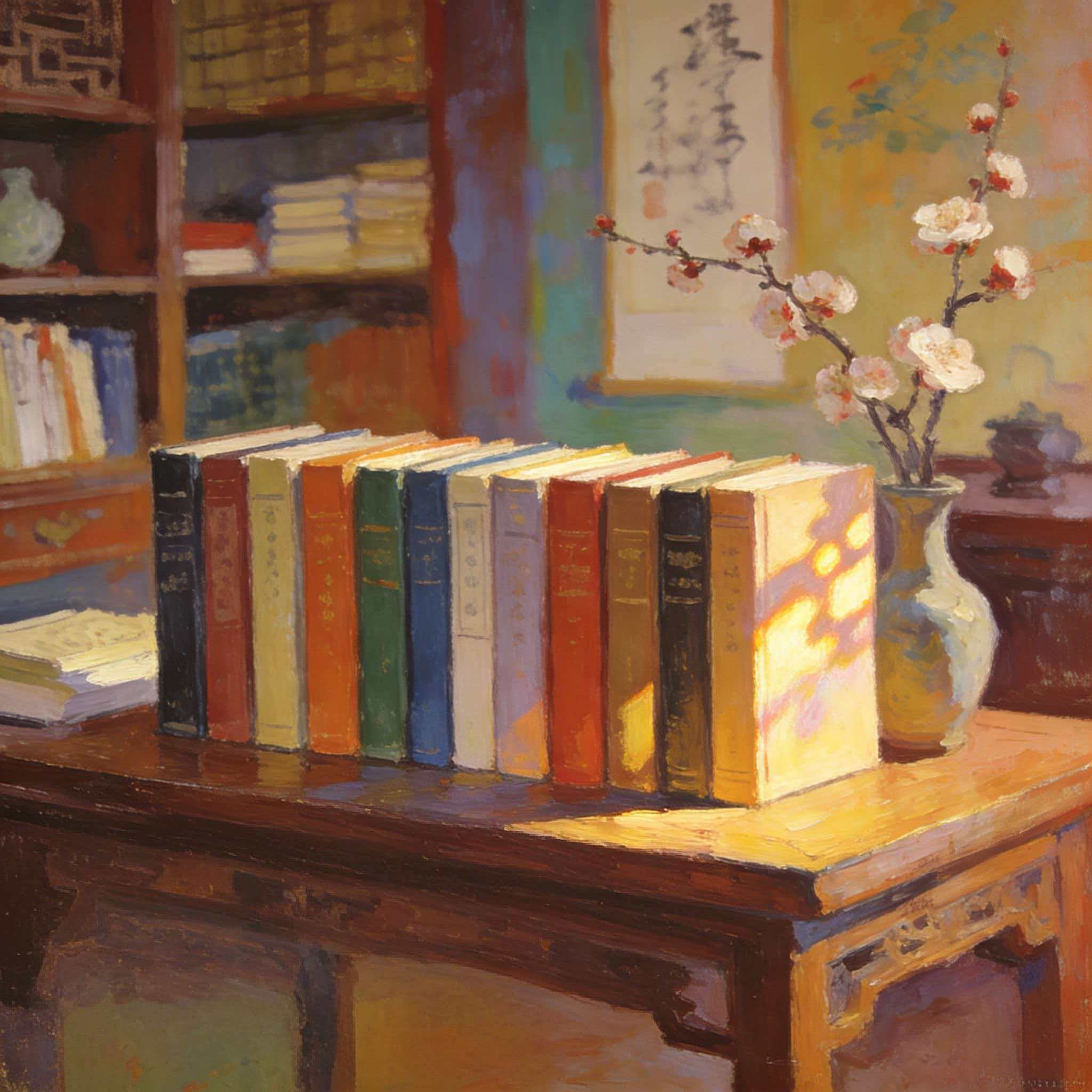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