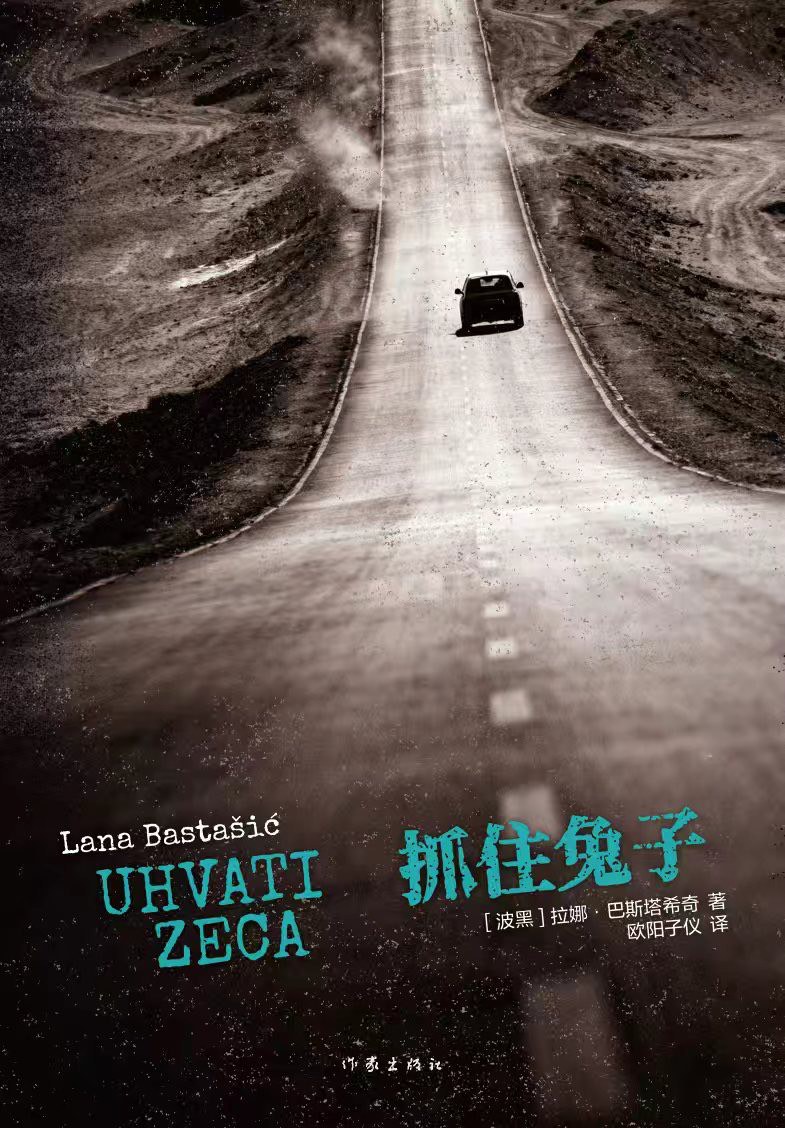
拉娜·巴斯塔希奇在《抓住兔子》中,用一场跨越国界的公路旅程,将读者引入巴尔干半岛的记忆迷宫。当远居都柏林的萨拉接到童年挚友蕾拉的电话,一句“阿尔明在维也纳”便打破了十二年的沉寂,也让两个女人踏上了既是寻找失踪兄长、亦是打捞被战争掩埋的童年的旅程。这部入围多项国际文学奖项的作品,如同一块亮起的雪花屏,模糊却真切地映照出战争对个体命运的碾压与历史创伤的代际回响。
小说最精妙的笔触,在于以“碎片化记忆”为叙事骨架,构建起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的共振。巴斯塔希奇没有采用线性叙事,而是让萨拉的记忆在现实与过往间反复跳转:埋葬兔子的童年午后、樱桃树下的秘密、邻居家莫名中毒的狗,这些零散的片段如同散落的拼图,在寻找阿尔明的途中逐渐拼凑出轮廓。“兔子”作为贯穿始终的核心隐喻,既是童年纯真的象征——蕾拉偷来的白色家兔承载着两人最亲密的时光,也是历史创伤的载体——活兔子的奔逃与死兔子的埋葬,暗合了巴尔干半岛在战乱中的撕裂与沉沦。这种叙事方式并非刻意炫技,而是精准复刻了创伤记忆的特质:那些不愿被记起的过往从未真正消失,只会在某个触发点的刺激下,以更汹涌的姿态重现。
女性友谊的复杂肌理与身份认同的困境,在旅程中被层层剥开。萨拉与蕾拉的关系,像极了费兰特笔下莱农与莉拉的羁绊——既有无法割舍的共生依赖,也有隐秘的竞争与伤害。蕾拉从“蕾拉·贝吉奇”到“莱拉·贝里奇”的姓名变迁,看似只是简单的称谓更改,实则是巴尔干民族分裂在个体身上的烙印——穆斯林姓名向塞尔维亚族姓名的转变,背后是无法调和的族群矛盾与身份撕裂。而这一转变恰好发生在两人初次月经的年纪,身体的出血与土地的流血形成残酷互文,将女性身体与巴尔干土地紧密绑定,暗喻着战争对个体生命与族群根基的双重侵蚀。当萨拉在维也纳的博物馆站在丢勒的野兔油画前,看着奔跑离去的蕾拉,终于读懂了这场寻找的本质:她们寻找的从来不是阿尔明,而是那个“无血而干净”的童年,是在民族与宗教仇恨中丢失的自我认同。
作为前南斯拉夫作家文学特质的延续,巴斯塔希奇用隐喻消解了历史叙事的沉重,却又让创伤的痛感直抵人心。她没有直接描绘战争的血腥场面,却通过“姓名被篡改”“语言被放弃”“故乡变陌生”等细节,让战争的后遗症无处不在。萨拉自愿放弃母语、在都柏林重构生活的努力,本质上是对创伤的逃避,而这场旅程则迫使她直面:那些被刻意遗忘的过往,早已成为身份的一部分。小说结尾的循环叙事极具深意,开头的“让我们从头开始”与结尾的“我们想要”形成闭环,暗示着巴尔干的历史困境与个体的创伤记忆,如同无法挣脱的漩涡,在代际间不断重演。
当然,小说的隐喻体系并非完美无缺。为了承载历史主题,蕾拉的人物行为有时显得过于刻意,其言行逻辑的割裂感让人物形象略显扁平,仿佛成为了隐喻的附属品而非鲜活的个体。但这并不影响作品的整体价值——巴斯塔希奇成功地用文学的方式,让不了解巴尔干历史的读者也能感受到创伤的重量。她证明了隐喻的力量:当直接的历史叙述难以触及真相时,个体的情感记忆与象征符号,反而能更精准地抵达历史的内核。
《抓住兔子》最终告诉我们,抓住兔子或许是不可能的——就像无法抓住流逝的童年与被撕裂的历史,无法让奔逃的蕾拉停下脚步,也无法让静止的萨拉重回过去。但这场寻找本身已具有意义:在记忆的碎片中,我们得以看见历史的真相;在友谊的羁绊中,我们得以确认自我的存在。巴斯塔希奇用细腻而充满张力的文字,为巴尔干的创伤写下了一曲温柔却有力的挽歌,也让每个读者在个体与历史的对照中,读懂记忆与救赎的真正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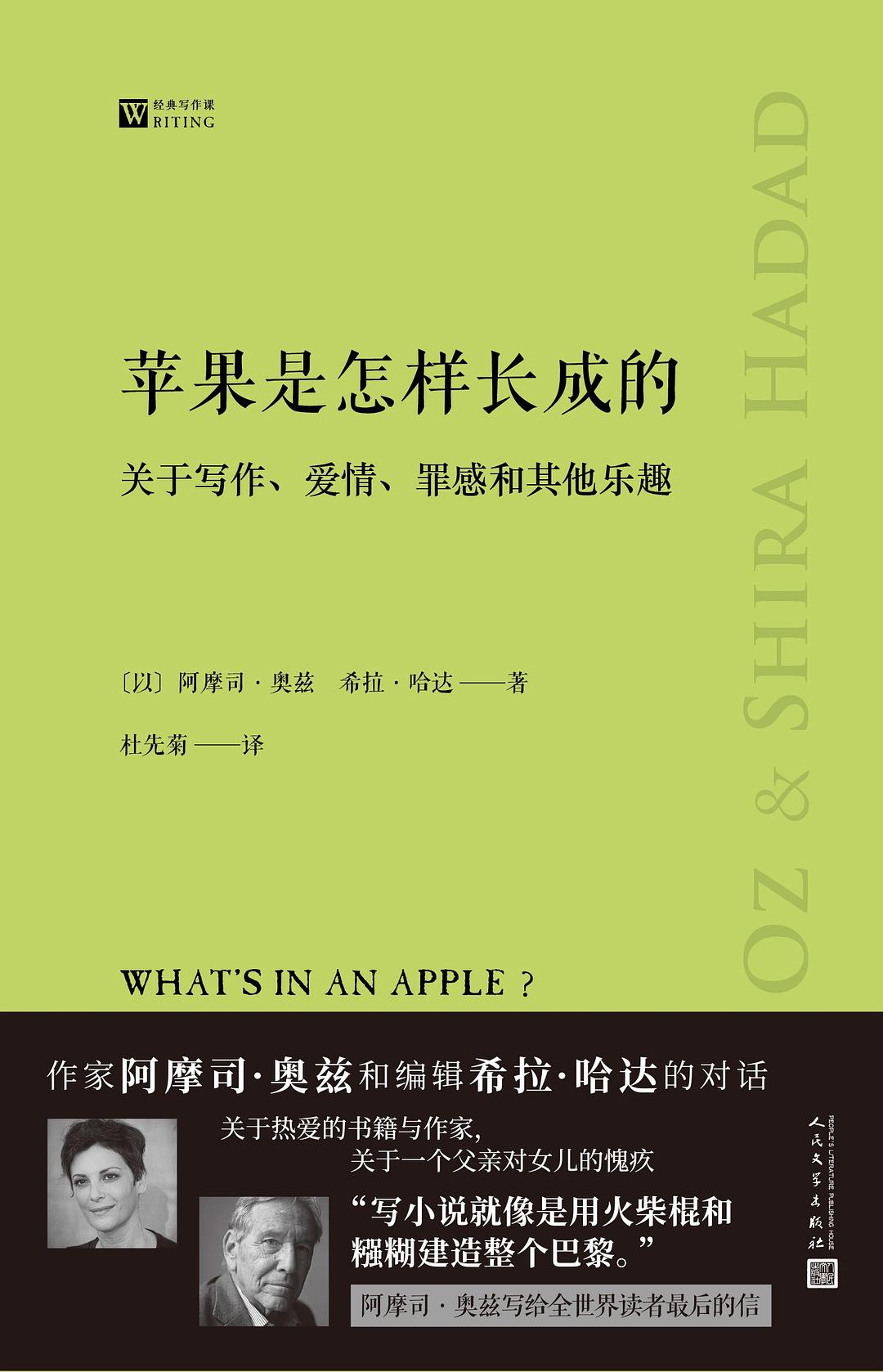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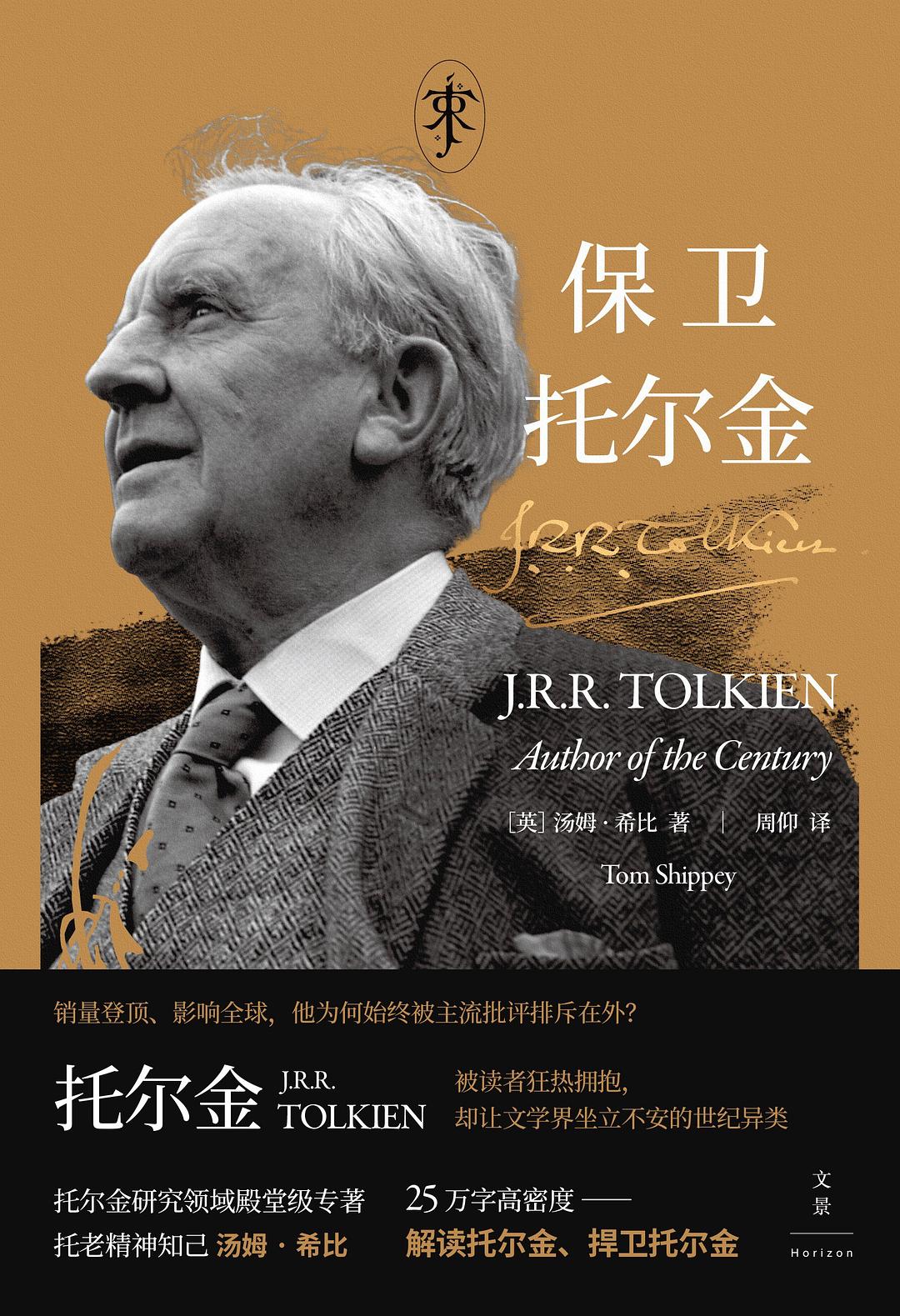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