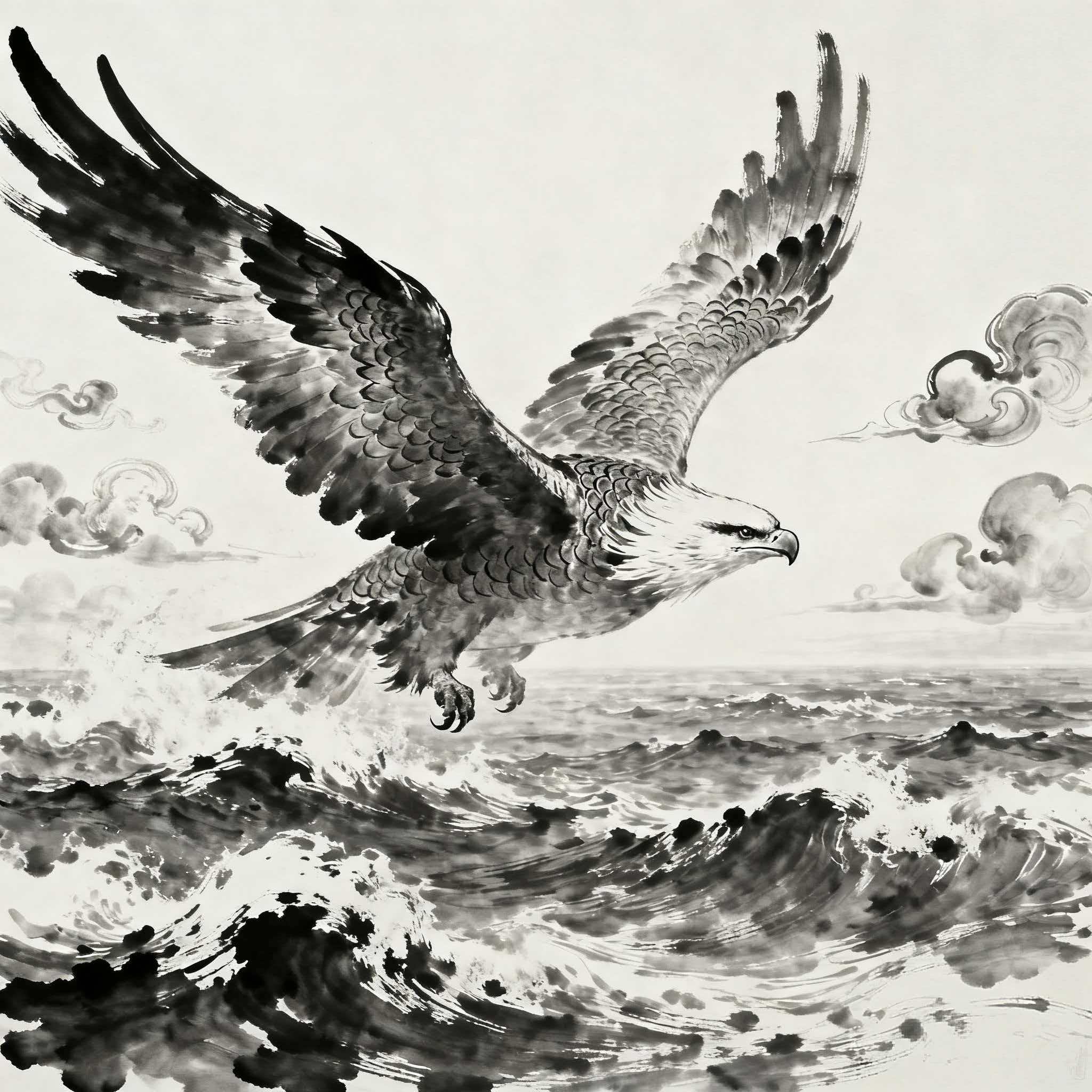《诗经》-三百里的风与月

翻开《诗经》的纸页,像推开一扇吱呀作响的木窗,风从两千多年前吹进来,裹着蒹葭的霜、桃花的香,还有田埂上农人哼着的调子,落在指尖,温软得能捏出水分来。
最先撞见的是《秦风·蒹葭》里的晨雾。“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读这八个字时,仿佛站在河岸边,秋露凝在芦苇叶上,白得像薄霜,风一吹,芦苇秆轻轻晃,雾里的人影若隐若现。没有浓墨重彩的描摹,只这一句,就把秋日清晨的清寂与怅惘,织成了幅淡墨画——后来见再多写秋雾的句子,都不及这两句来得清透,像含在嘴里的薄荷,凉丝丝的,却余味绵长。
再往下翻,是《周南·桃夭》里的春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四月的桃花该是这样的吧?开得热烈,像姑娘颊上的胭脂,一簇簇压满枝头,风过处,花瓣簌簌落,落在新嫁娘的红嫁衣上。没有复杂的比喻,只“灼灼”二字,就把桃花的艳、春日的暖,还有新婚的喜,都揉在了一起。仿佛能看见送亲的队伍走过桃树下,姑娘笑着,鬓边别着朵刚摘的桃花,连空气里都飘着甜。
还有《郑风·风雨》里的暖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雨打着窗棂,天色暗得像墨,鸡在院里不停地叫,心也跟着慌。可门“吱呀”一声开了,那个等了许久的人站在门口,衣角沾着雨,却笑着说“我回来了”。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话,只一句“云胡不喜”,把所有的牵挂、委屈、欢喜,都揉成了心口的热。后来每逢雨天,总想起这两句,觉得最踏实的幸福,不过是风雨里,有人为你撑着伞,等你回家。
《诗经》里的美,从不是铺张的。是“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里,农妇弯腰采车前草的轻快;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里,小鹿在草地上鸣叫的悠然;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里,战士握着爱人的手,许下的朴素诺言。它写的是寻常日子里的风、花、雨、露,是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却像窖藏的酒,越品越醇。
合上书时,窗外的风正吹过树梢,像《诗经》里的调子,轻轻晃。原来那些两千多年前的情感,从未走远。风里的蒹葭、枝头的桃花、雨里的等待,还在我们的日子里活着——这就是《诗经》的美,它把最真的生活,写成了最久的诗,让我们每次翻开,都能遇见心里的那片风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