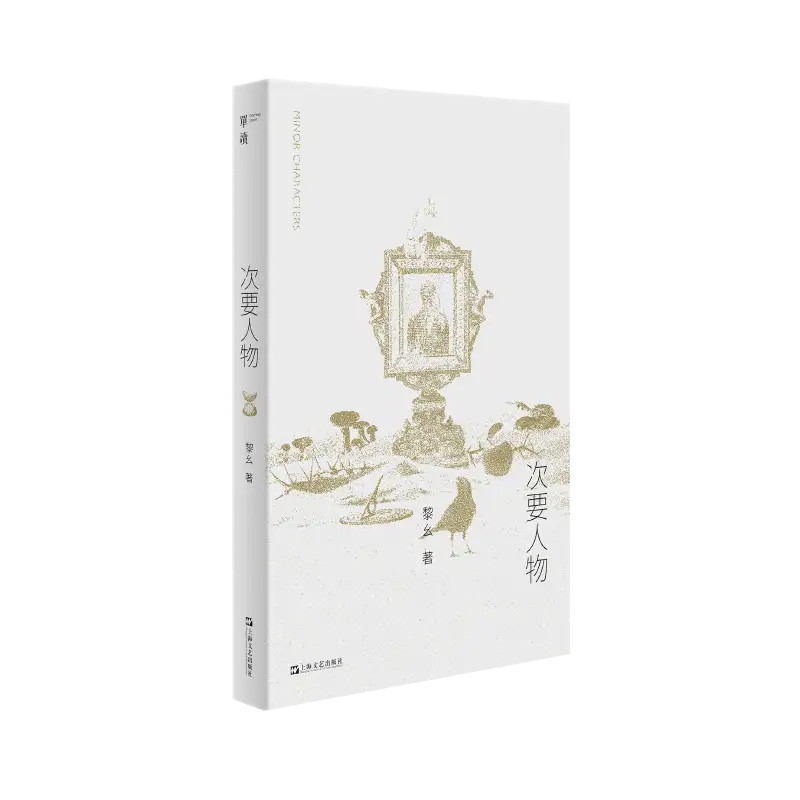
当文学市场热衷于追逐宏大叙事与强烈戏剧冲突时,黎幺却在《次要人物》中调转目光,将镜头对准了生活里那些“不被看见”的普通人。这本短篇小说集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自带光环的主角,只静静铺陈着快递员、便利店店员、退休老人的日常碎片——但正是这些细碎的、甚至有些平淡的瞬间,被黎幺以细腻的笔触串联成诗,让我们在“次要人物”的世界里,重新触摸到日常的重量与温度。
黎幺笔下的“次要”,从不是“边缘”的代名词,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生活切面。书中没有明确的主角姓名,更多时候,人物只以“快递员小吴”“便利店夜班店员”“住在老楼三层的张姨”这样的身份标签存在,就像我们每天擦肩而过、却从不停留打量的陌生人。在《晚班日志》里,夜班店员用一本笔记本记录下深夜到店的顾客:醉酒后絮叨着工作压力的年轻人、反复核对购物清单的独居老人、偷偷给孩子买零食的单亲妈妈;这些片段没有开端与结局,却像一帧帧生活快照,将现代人的孤独、疲惫与微小的温柔,藏在“扫码付款”“整理货架”的日常动作里。黎幺从不用刻意的煽情,只客观呈现人物的言行与心理,可恰恰是这种“不干预”的书写,让读者在字里行间看见自己的影子——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藏着这么多未被言说的情绪。
更难得的是,黎幺总能在“平淡”中挖出日常的“褶皱”,让看似重复的生活显露出隐秘的质感。《老楼的下午》里,退休老人每天的生活就是在阳台浇花、下楼取报纸、在小区长椅上坐一会儿,可黎幺却捕捉到了这些动作里的细节:老人浇花时会特意避开最娇弱的那株月季,取报纸时会顺手把邻居家歪倒的牛奶箱扶正,坐在长椅上时会偷偷观察路过的孩子,想起自己早逝的孙子。这些细微的举动,没有推动任何“剧情”,却让人物瞬间立体起来——老人的孤独不是空洞的“寂寞”,而是藏在“避开月季”的温柔里,藏在“扶正牛奶箱”的善意里,藏在“望向孩子”的思念里。黎幺像一位耐心的观察者,把我们忽略的日常细节放大,让我们发现:原来平凡的生活从不是“一片空白”,而是布满了褶皱,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一个人的心事与过往。
《次要人物》最动人的力量,在于它让“次要”拥有了“主角感”。在传统叙事中,这些人物或许只是推动主角故事的“工具人”,可在黎幺的笔下,他们的喜怒哀乐成了绝对的核心。《快递单》里,快递员小吴因为送错一个包裹,反复联系收件人道歉,不是因为怕被投诉,而是因为收件人是一位独居老人,他担心老人着急——这个看似“多余”的举动,没有改变任何“大事”,却让小吴这个“次要人物”有了光芒。黎幺从不试图给人物“贴标签”,也不强行赋予他们“崇高”的意义,只是让他们自然地生活、自然地流露情绪,这种“不刻意”的书写,反而让“次要人物”的形象更显真实: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梦想,只希望按时下班、家人平安;他们会为一点小事纠结,也会因一点善意感动,就像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合上书页时,窗外或许正上演着书中的场景:快递员骑着车穿梭在街道,便利店的灯还亮着,老人们在小区里散步。黎幺用《次要人物》告诉我们,文学不只是书写英雄与传奇,更应该关注这些“日常里的人”——他们或许没有响亮的名字,没有波澜壮阔的人生,却用自己的方式认真生活着。这些“次要人物”的故事,就像散落在日常里的微光,看似微弱,却汇聚成了生活最真实的模样。对于习惯了快节奏阅读的我们来说,《次要人物》更像一本“慢读指南”,它让我们放慢脚步,去观察身边的人、去感受日常的细节——毕竟,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次要”,或许正是生活最珍贵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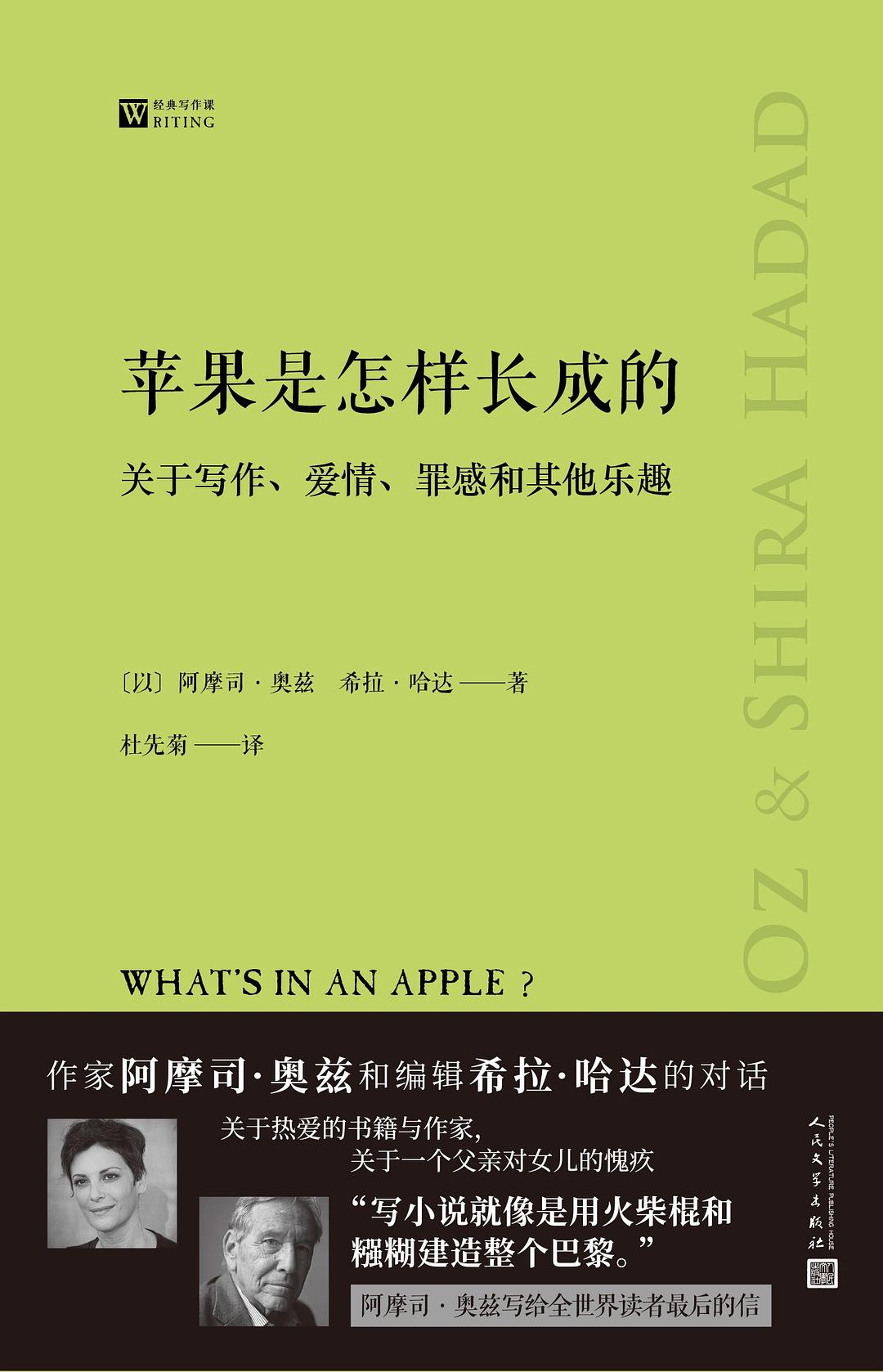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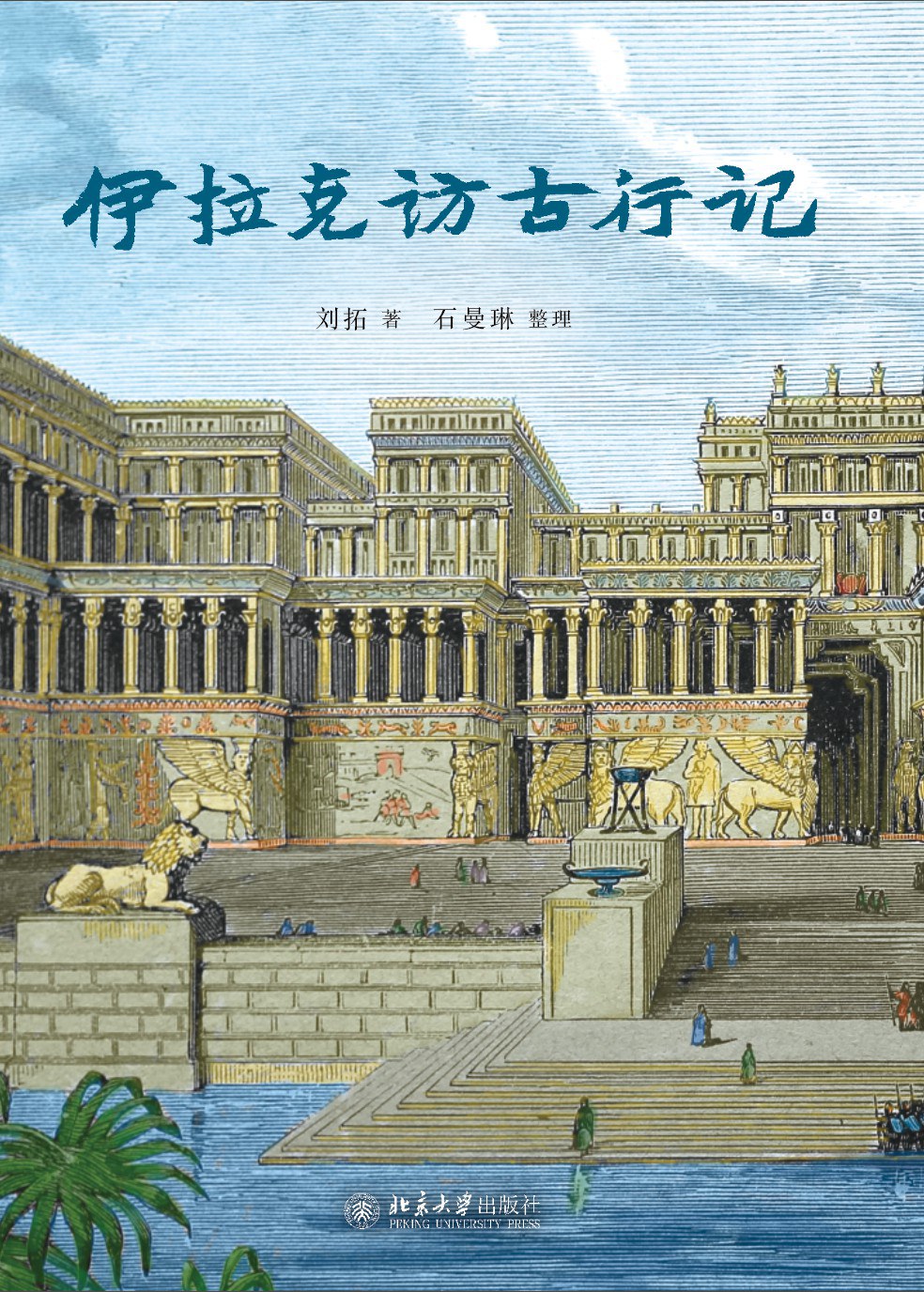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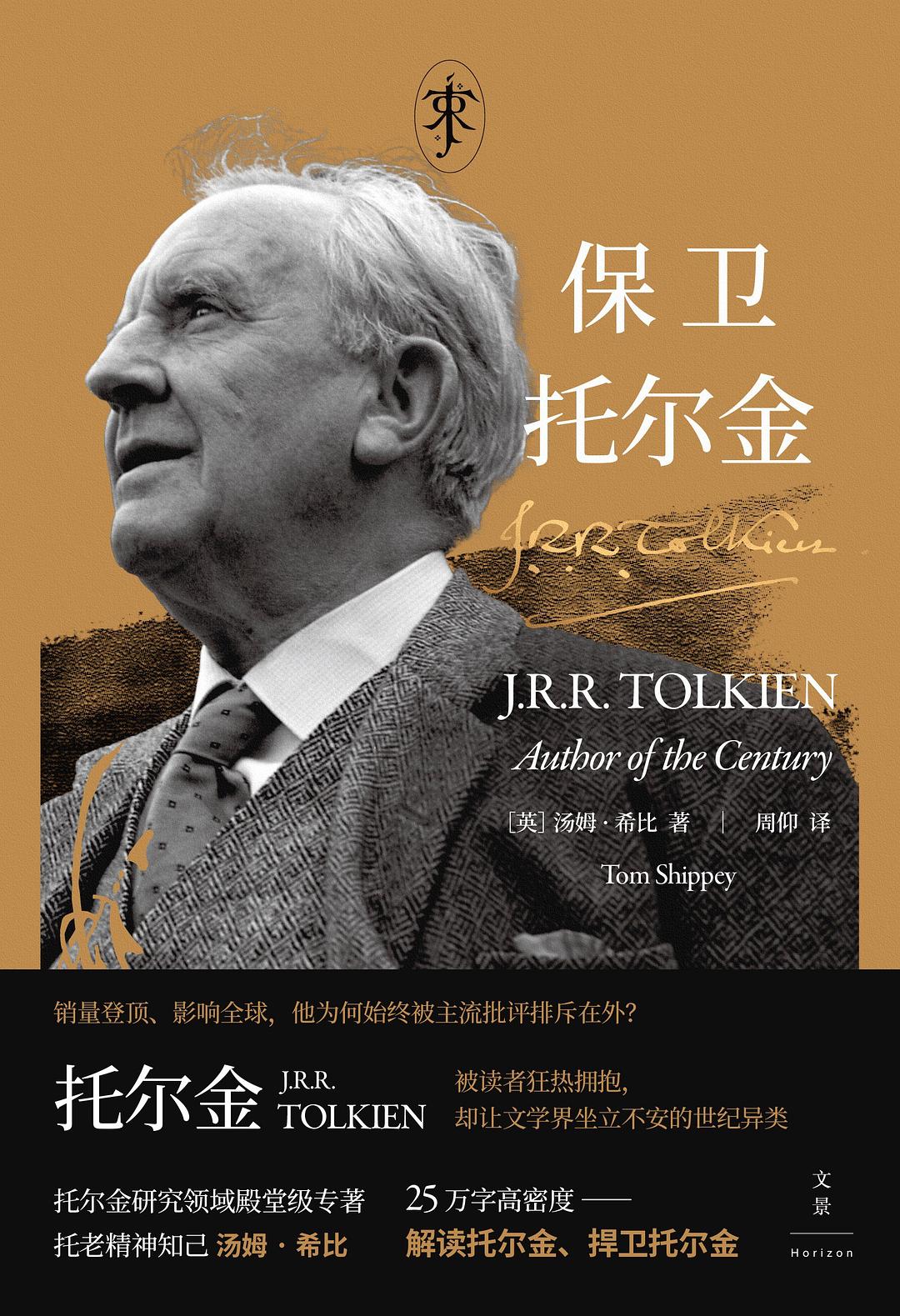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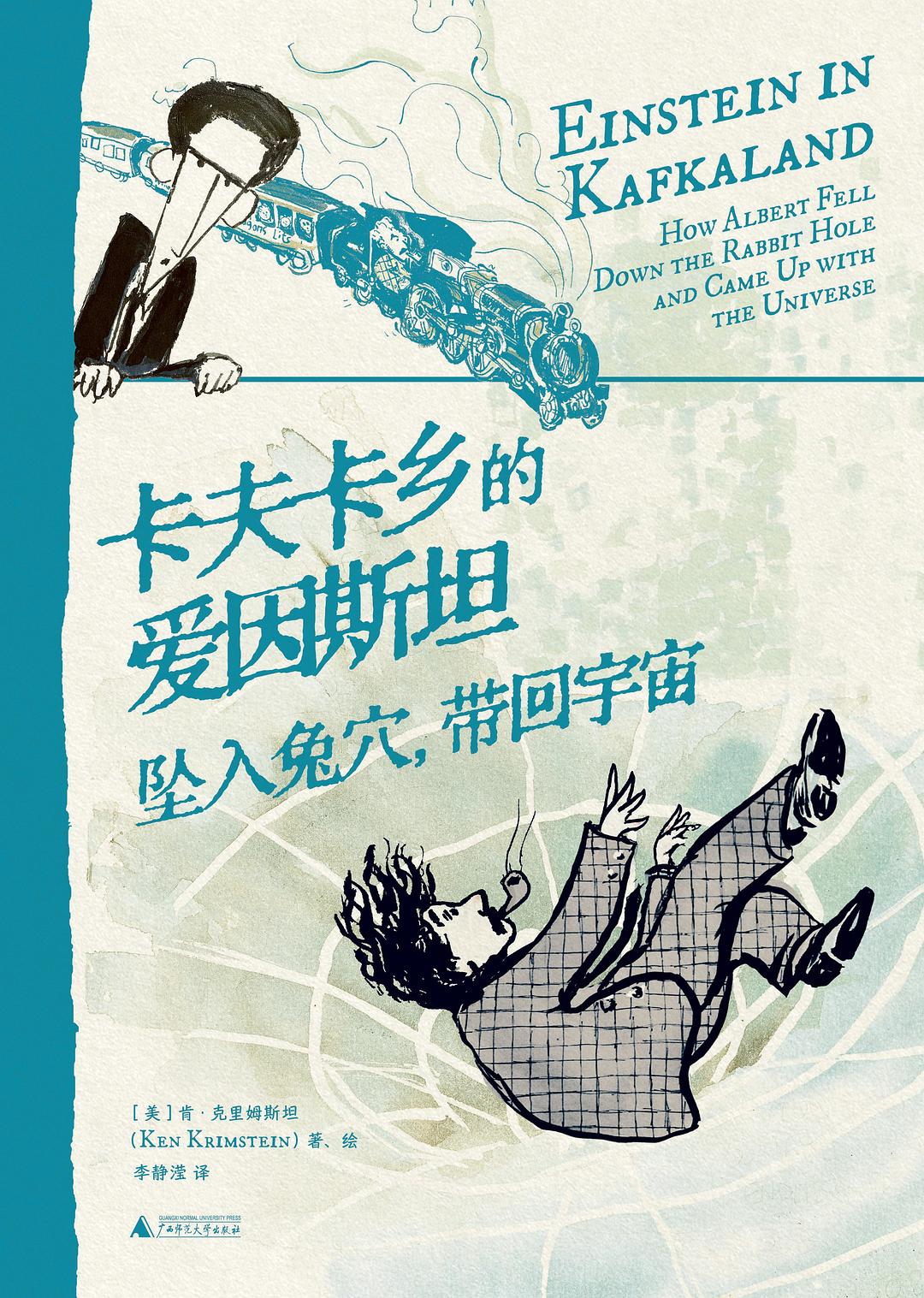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