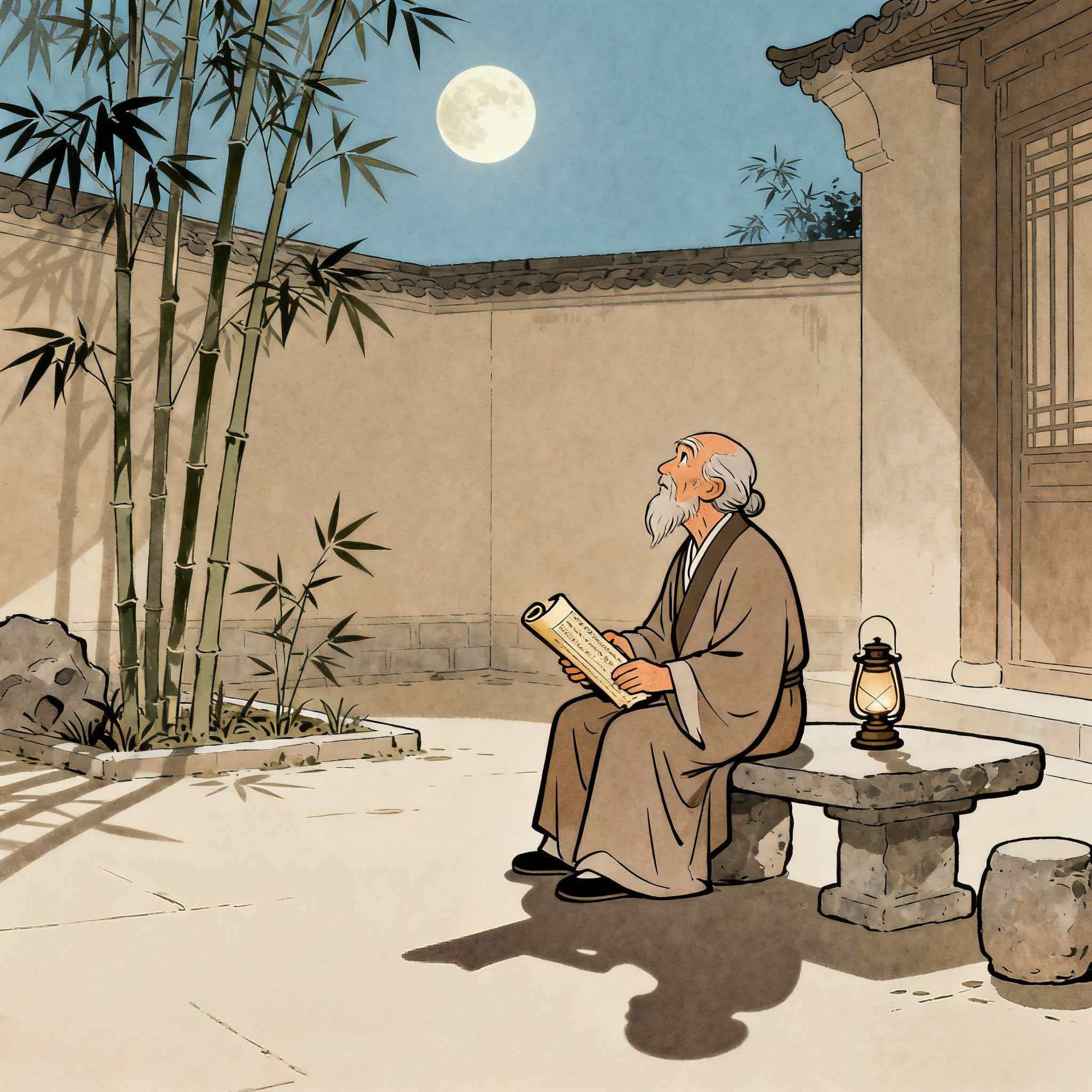千里马的悲鸣与时代的叩问——评《马说》

韩愈的《马说》,以短短数百字的寓言,道尽了人才被埋没的千古痛惜。它既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文以载道”的典范,更以犀利的隐喻,刺穿了封建时代“人才遇合”的困境,成为跨越千年仍振聋发聩的人才悲歌。
一、以“马”喻“人”:极简寓言里的深刻批判
《马说》最精妙之处,在于用“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构建起一套直指现实的隐喻体系,以动物寓言的外壳,包裹对人才命运的沉痛思考,字字看似谈马,实则论人。
开篇“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句便定下全文的核心矛盾——人才的价值,需靠“识才者”来发掘;但现实中,能慧眼识珠的“伯乐”,远比资质出众的“千里马”罕见。这看似简单的判断,实则是对封建官场“任人唯亲、埋没贤才”的尖锐批判:不是时代无才,而是掌权者缺乏识才的眼光与用才的胸怀。
文中对千里马遭遇的刻画,更是将这种“埋没之痛”写得入木三分。“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本应驰骋千里的良驹,却被当作普通马喂养,最终在马厩中默默死去,连“千里马”的名号都无人知晓——这正是无数怀才不遇者的命运缩影:有经天纬地之才,却困于底层、屈于庸人,终其一生不得施展。
更令人痛心的是“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的诘问。千里马因“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连基本的粮草都得不到满足,连普通马的水平都难以达到,何谈发挥“千里之能”?这背后,是韩愈对“用才者”的强烈控诉:他们不仅不识才,更不会育才、用才,甚至以对待“常马”的方式对待“千里马”,最终让人才的光芒被彻底遮蔽。全文以“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收尾,用反问强化情感,将“不知马”的批判从“食马者”个体,上升到整个时代的痼疾,余味绵长,引人深思。
二、文外有“愤”:寒门士子的命运呐喊
《马说》的力量,不止于隐喻的精巧,更在于其背后韩愈个人的“切肤之痛”。这篇文章作于韩愈早年仕途失意之时——他出身寒门,自幼苦读,二十五岁中进士,却因无人举荐,连续三次参加吏部考试均告失败,只能四处奔走求告,迟迟不得官职。
文中千里马的“悲鸣”,正是韩愈自身的“愤懑”。他深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残酷:唐代虽有科举制,但门阀制度仍根深蒂固,权贵子弟凭借家世轻易得官,而寒门士子即便才华横溢,若无人赏识举荐,也只能空怀壮志、潦倒一生。他笔下“食马者”的“无知”与“傲慢”,正是对那些手握权柄却昏庸无能、埋没人才的官员的批判;而千里马的“辱”与“死”,则是他对自身命运的担忧,更是对整个寒门士子群体遭遇的同情。
这种“愤懑”并非消极的抱怨,而是积极的呐喊。韩愈一生都在为“人才”发声,他主张“唯才是举”,反对“任人唯亲”,即便后来官至高位,仍不忘提拔后进。《马说》正是他这种理念的集中体现:**人才是时代的瑰宝,而识才、用才,是掌权者的根本责任**。
三、千古共鸣:跨越时代的人才之思
《马说》之所以能流传千年,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在于它触及了一个永恒的命题——“人才与机遇”的关系,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种“怀才不遇”的困境与“渴望被赏识”的心声,总能引发人们的强烈共鸣。
从古至今,无数有才华的人,都曾经历过“千里马”的困境: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却被流放汨罗;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却终其一生未能实现北伐之志;即便是现代社会,“怀才不遇”“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仍时常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而《马说》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了这种困境,更在于它提醒人们:一方面,“伯乐”的重要性——掌权者需有识才的眼光、用才的魄力,为人才搭建施展的平台;另一方面,“千里马”也需有“毛遂自荐”的勇气,在机遇来临时主动展现自己的价值。
在今天,《马说》依旧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它提醒我们:一个时代的进步,离不开对人才的重视;而个人的成长,既需锤炼“千里之才”,也需学会寻找“伯乐”、把握机遇。这篇短小的寓言,早已超越了唐代的时空,成为一曲跨越千年的“人才赞歌”与“时代叩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