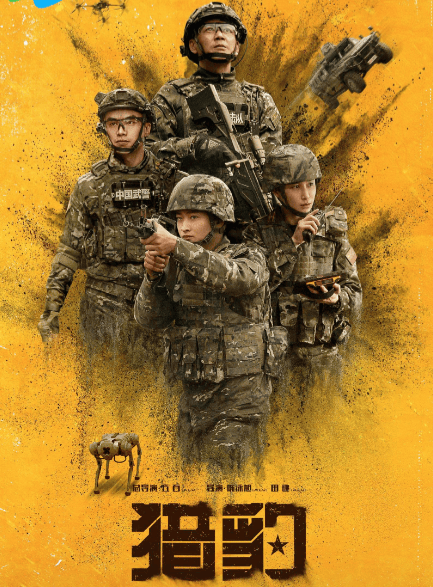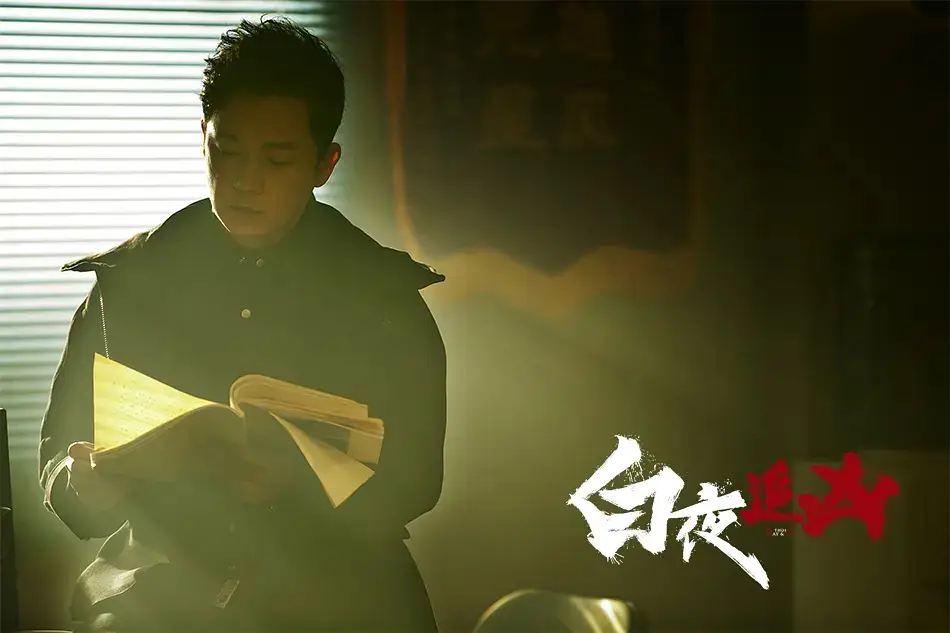《生万物》:土地叙事下的时代褶皱与人性叩问——一部争议中探寻乡土深度的年代剧

在国产年代剧创作日益追求“史诗感”与“烟火气”平衡的当下,聚焦20世纪鲁南农村的《生万物》以“土地”为核心命题,试图剖开农耕文明的肌理,还原特定历史阶段下农民的生存图景与命运沉浮。这部剧自开播起便裹挟着赞誉与争议:有人盛赞其对乡土细节的还原、对人性复杂的刻画;也有人诟病其历史真实感的偏差、人物塑造的违和。然而,正是这些多元声音,让《生万物》超越了一部普通农村剧的范畴,成为一面映照年代剧创作困境与突破方向的镜子。
一、土地:从“生存根基”到“精神图腾”的主题深挖与遗憾
《生万物》最鲜明的创作底色,是将“土地”置于叙事的绝对核心——它不再是背景板,而是推动剧情、塑造人物、承载主题的“隐形主角”。剧集开篇便以鲁南天牛庙村的土地为锚点:地主宁学祥(倪大红 饰)的案头永远摆着地契匣子,手指摩挲着泛黄的纸页时,眼神里的贪婪与敬畏几乎要溢出屏幕;自耕农封二(杨新鸣 饰)为了多攒半亩地,顶着烈日在田里劳作到腰杆再也直不起来,临终前还攥着沾泥的锄头,反复叮嘱儿子“地是根,丢了根就没了魂”;佃户们春耕时跪在田里播撒种子,动作虔诚得像在进行一场仪式,秋收时看着粮囤的眼神,比看自家孩子还温柔。
这些细节精准戳中了农耕文明的核心逻辑:土地不仅是“能长出粮食的泥巴”,更是身份的象征(地主与佃户的界限由土地划分)、家族的传承(宁家的地契传了三代)、生存的底气(封家靠几亩薄田熬过灾年),甚至是精神的信仰(农民对土地的敬畏,不亚于对神明的崇拜)。剧集通过不同阶层对土地的态度差异,悄然勾勒出20世纪20-40年代鲁南农村的社会结构:宁学祥代表的地主阶层,将土地视为“权力的筹码”,他们囤积土地、收取地租,却也在灾年时不得不靠土地维系家族体面;封二这样的自耕农,将土地视为“安稳的保障”,他们一生的目标就是“多一亩地、多一口粮”;而无地的佃户,则将土地视为“生存的希望”,他们依附地主的土地,却也在土地上透支着自己的一生。
遗憾的是,剧集对“土地变革”这一关键命题的处理,却显得仓促而浅白。20世纪30-40年代,鲁南地区经历了土地政策的初步调整,部分农村开始尝试“减租减息”,甚至出现早期土地改革的萌芽——这原本是展现“土地如何改变农民命运”的最佳切口,也是深化“土地主题”的核心环节。但剧中仅通过几句台词提及“县里来了新政,地租能少交两成”,既没有展现佃户得知消息时的震惊与犹豫(担心地主报复)、地主的抗拒与妥协(不愿放弃既得利益),也没有刻画土地政策落地后农村社会关系的微妙变化(佃户与地主的关系是否缓和?自耕农是否有机会获得更多土地?)。原本能让“土地主题”从“静态描摹”走向“动态变革”的关键情节,最终沦为背景板,使得“土地如何影响时代”的深度探讨,停留在了“土地很重要”的表层认知上。
二、人物:群像的鲜活与主角的违和,折射年代剧的表演困境
《生万物》的人物塑造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配角群像鲜活得如同从鲁南农村走出来的真人,而主角的表演却时常让人出戏,这种反差恰恰暴露了年代剧创作中“流量演员与角色适配度”的核心矛盾。
配角阵营中,倪大红与秦海璐的表演堪称“教科书级别”。倪大红饰演的宁学祥,打破了“地主必是凶神恶煞”的刻板印象:他抠门到给女儿做嫁妆时只肯用粗布,却会在灾年时悄悄给佃户留半袋种子;他为了保住土地,不惜牺牲女儿宁绣绣(杨幂 饰)的幸福,却在女儿被土匪劫走后,躲在书房里偷偷抹眼泪。倪大红没有用夸张的表情或台词塑造角色,而是通过“捏地契时指节发白”“算地租时眼神闪烁”“独处时佝偻的背影”等细节,将一个“贪婪却不恶毒、固执却有软肋”的复杂地主形象立了起来——他不是“坏人”,而是被“土地执念”绑架的可怜人。
秦海璐饰演的费左氏,则是另一种复杂的女性形象。作为寡妇,她撑起了费家的家业,既要应对宁学祥这样的地主施压,又要安抚家里的老弱妇孺;她对长工苛刻,却会在长工生病时请郎中;她看不起佃户的“穷酸”,却在佃户被土匪欺负时,悄悄报官。秦海璐用略带沙哑的嗓音、锐利却藏着疲惫的眼神,将这个“在封建礼教与生存压力中挣扎的女性”演绎得入木三分——她的“狠”是被逼出来的,她的“善”是藏在骨子里的。此外,杨新鸣饰演的封二、刘丹饰演的宁母,甚至只有几句台词的老佃户,都带着鲁南农村特有的“土味”与鲜活,他们的方言、动作、神态,让观众仿佛真的置身于那个烟火气十足的村庄。
相比之下,主角杨幂与欧豪的表演则显得“悬浮”。杨幂饰演的宁绣绣,是地主家的娇小姐,后来因家族变故嫁给自耕农封大脚(欧豪 饰),成为农家媳妇。这个角色的核心是“转变”——从养尊处优到下地劳作,从娇纵任性到坚韧隐忍。但杨幂的表演,始终没能突破“偶像滤镜”:即便宁绣绣已经沦为农家妇,她的皮肤依旧白皙细腻,妆容精致到睫毛根根分明,甚至在田里插秧时,衣服也干净得没有半点泥点;她试图通过“皱眉”“低头”表现角色的委屈与隐忍,却缺乏眼神里的“土气”与“韧劲”,让“娇小姐变农妇”的转变显得像“体验生活”,而非“真正扎根土地”。
欧豪饰演的封大脚,问题则在于“用力过猛”。为了展现庄户汉子的“憨厚”,他刻意放慢语速、压低声音,却忘了“憨厚”不是“木讷”;为了表现角色的“勤劳”,他在田里扛锄头时,动作僵硬得像在“摆拍”,缺乏长期劳作形成的“肌肉记忆”。更关键的是,他与杨幂的对手戏,始终没有化学反应——两人饰演的夫妻,更像“城里来的演员在演农村夫妻”,而非真正在土地上共患难的伴侣。这种“主角违和、配角出彩”的现象,不仅让人物关系失去了可信度,也让剧情的情感张力大打折扣。
三、剧情:戏剧冲突与历史真实的失衡,暴露年代剧的创作难题
《生万物》的剧情编排,呈现出“开篇抓眼、中段疲软、结尾仓促”的节奏问题,而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戏剧冲突”与“历史真实”的失衡——为了追求“好看”,剧集刻意强化了情节的戏剧性,却忽视了历史背景的合理性,最终让故事沦为“披着年代外衣的狗血剧”。
剧集开篇的冲突设计堪称巧妙:宁绣绣成亲当天,被土匪劫走,父亲宁学祥舍不得卖地赎女,只能让二女儿替嫁;宁绣绣被救回后,家族已然败落,她不得不嫁给“穷小子”封大脚;封大脚的父亲封二,为了给儿子攒彩礼,拼命劳作最终累死在田里。这一系列情节,既串联起地主、自耕农、土匪等不同群体,又快速建立了人物关系与矛盾,让观众迅速代入剧情。前10集,剧情节奏紧凑,冲突迭起:宁绣绣与封大脚的“阶级矛盾”(娇小姐看不起穷汉子)、宁学祥与费左氏的“利益争夺”(争夺村里的水源)、村民与土匪的“生存对抗”,每一个冲突都紧扣“土地”与“生存”,既有戏剧性,又符合历史背景。
但从第15集开始,剧情逐渐偏离“土地叙事”,转向“家庭伦理”与“狗血爱情”:宁绣绣与封大脚的婆婆矛盾不断,从“做饭咸淡”到“带孩子方式”,鸡毛蒜皮的小事被反复渲染,却对“土地收成”“地租变化”等关键情节一笔带过;封大脚的妹妹被地主家的儿子看上,两人上演“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爱情,却完全忽视了“地主与自耕农阶层差异”的历史现实;甚至加入“宁绣绣被冤枉偷东西”“封大脚被诬陷通匪”等套路化情节,让剧情变得冗长且脱离主题。
更严重的是,剧集对“历史真实”的忽视,让故事失去了年代剧应有的“厚重感”。一方面,场景还原失真:1926年的鲁南农村,普遍是土坯房、茅草顶,而剧中的天牛庙村,却满是青砖瓦房、石板路,甚至出现了只有现代才有的塑料薄膜大棚、彩钢瓦房,这些“穿越”道具严重破坏了时代沉浸感;另一方面,历史逻辑混乱:剧中地主宁学祥被塑造成“体恤佃户”的“好地主”,灾年时主动减免地租,甚至给佃户送粮,这与历史上地主对佃农的残酷剥削(地租通常占收成的50%-70%,灾年也极少减免)严重不符,弱化了“土地兼并”的残酷性,也模糊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这种“为了温情而牺牲真实”的创作选择,让《生万物》的历史叙事失去了根基,沦为一部“美化封建农村”的偶像剧。
四、结语:年代剧的“根”,永远在真实与深度里
《生万物》的争议,本质上是国产年代剧创作困境的缩影:当“流量演员”与“历史真实”冲突时,该如何选择?当“戏剧冲突”与“主题深度”矛盾时,该如何平衡?这部剧给出的答案,显然并不完美——它为了迎合流量,牺牲了主角的适配度;为了追求好看,弱化了历史的真实性;为了营造温情,放弃了主题的深度。但即便如此,《生万物》依然有其价值:它试图以“土地”为核心,构建农耕文明的叙事体系,这种尝试本身就值得肯定;它塑造的宁学祥、费左氏等配角,为年代剧的人物塑造提供了“复杂而非刻板”的范本;它暴露的问题,也为后续年代剧创作敲响了警钟。
对于年代剧而言,“年代”从来不是噱头,“真实”才是底色;“剧”从来不是空洞的壳,“深度”才是灵魂。无论是《白鹿原》对土地与家族的深刻剖析,还是《人世间》对平民命运与时代变迁的细腻描摹,优秀的年代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它们扎根于历史的土壤,关注人的生存与情感,挖掘时代的褶皱与人性的深度。《生万物》的遗憾,恰恰在于它没能守住这份“根”——它有土地的“形”,却没有土地的“魂”;它有人物的“壳”,却没有人物的“骨”;它有时代的“表”,却没有时代的“里”。
未来的年代剧创作,若能从《生万物》的争议中汲取教训,少一些流量依赖,多一些角色适配;少一些狗血套路,多一些历史敬畏;少一些表层描摹,多一些深度挖掘,或许就能创作出真正“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作品,让观众在光影中,真正读懂这片土地的厚重,读懂这个时代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