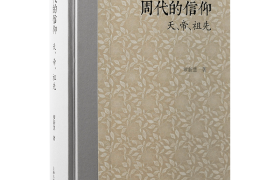摘 要:“《春秋》之诗”是理解杨维祯古乐府的重要维度,反映出其诗与《春秋》的密切联系及其强烈的诗教追求。在诗体认知方面,杨维祯将古乐府体视作风雅余韵,要求其承续《诗大序》构建的诗教传统。在知识渊源方面,《春秋》学中“君子原心”、重视“正统”等观念和注重褒贬善恶的旨趣,影响了杨维祯古乐府的写作内容。在诗教表达方面,杨维祯重视古乐府长于代言、叙事的特质,表现古之“情性”,形成其诗史式的诗教风格。杨维祯的古乐府代表了诗教传统在元末的新变。
关键词:杨维祯 古乐府 铁雅体 《春秋》学
杨维祯(1297—1370),字廉夫,乃元末文章巨擘,他和同道所鼓吹的“铁雅体”在元后期诗史中具有“范式”意义,代表了元诗最后的创变。[1]杨维祯的“铁雅体”主要是他所看重的“古乐府”一体,其以瑰丽奇崛著称,这又与杨氏狂狷求奇的个人性情相映衬,与杨氏得罪名教甚或被斥为“文妖”[2]的声名相勾连,从而显示出某种世俗性、反传统的特征。但这种理解势必将杨维祯及其创作扁平化,尤其是会忽视其古乐府诗中强烈而特殊的诗教追求。弟子金信评论杨氏之作说:“或议铁雅句律本屈、柳《天问》,某曰非也。属比之法,实协乎《春秋》。先生之诗,《春秋》之诗欤?诗之《春秋》欤?”杨氏对此议论至为认可,效仿孔子答子贡,曰:“信可与言诗已。”[3]此中消息,显示出《春秋》与杨维祯古乐府之间的莫大关系,更为理解其诗教理想提供了线索。 通过“《春秋》之诗”的视角,足以发现一条贯穿杨氏诗学观念、古乐府创作的暗线,以及因之浮现的诗教追求,也为认识杨维祯、“铁雅体”的丰富性及诗教传统在元末的新变提供了可能。鉴于前人对此言之甚少,本文试论述之。[4]

杨维桢像
一
承续诗教:杨维祯对古乐府的诗体认知
杨维祯最著名的诗体是古乐府,这也是其数量最夥、成绩最巨的诗体,但其对古乐府的定义和理解都具有自家面目。 他将古乐府视为承续《诗经》风雅传统的诗体,从而与“《诗》亡而后作”的《春秋》有会通之处,诗人也因之必须承担起诗教职能。杨维祯对古乐府的诗体认知,构成了理解“《春秋》之诗”这一诗学批评的第一个层次。
在元末,古乐府经杨维祯倡导而风靡东南诗坛,但他对“古乐府”诗体的界定与前人习用的古乐府概念颇有出入。自唐人兴起“新乐府”运动后,“古乐府”一般被用以指汉魏乐府古题。尽管杨维祯从未专门定义过其古乐府的诗体范畴,但从其概念使用和诗集编纂情况可以看出,其古乐府实际囊括了汉魏乐府古题、唐人乐府新题或诗题、自制新题等多种文类。[5]从数量上看,自制新题还占据了绝大多数。[6]不仅用题宽泛,其“古乐府”概念涵括的诗歌体制也很广,除了长短句,还包含了许多五绝七绝、五古七古作品。黄仁生因此概括指出,杨维祯的“古乐府”概念“除将律诗(包括排律)排斥在外,基本上兼备众体”[7]。若从天历元年(1328)他与同道李孝光开始以这种“古乐府辞”相唱和算起,他写作古乐府逾四十年,留存作品一千二百余首,形成“铁雅派”成员以百数[8],这都推动了其“古乐府”概念的流行与接受。
理解杨维祯的古乐府概念须从“乐府”与“古”两个方面进入:“乐府”主要是与律诗等诗体相对举,其边际首先表现为体制、语体等外在体貌的分别;而“古”则与“今”相对举,其边际首先凸显的是体性等内部审美精神的取舍。[9]研究者多从前者分析其古乐府的诗学艺术,而对后者较为忽略。但在“古”“今”的轩轾中,尤能看出杨维祯对古乐府诗体的价值认定。元代以“今乐府”指称曲,而杨维祯的古今划分寄寓着价值判断,包含有“正名”之旨。例如,他在《周月湖今乐府序》中说:“夫词曲本古诗之流,既以乐府名编,则宜有风雅余韵在焉。苟专逐时变,竞俗趋,不自知其流于街谈市谚之陋,而不见夫锦脏绣腑之为懿也,则亦何取于今之乐府、可被于弦竹者哉!”[10]从词曲出于古诗的诗体源流上,杨维祯要求“乐府”应有风雅余韵、不能竞趋于俗。在《沈氏今乐府序》中,他更是认定“今乐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尤其“迩年以来,小叶俳辈类以今乐府自鸣,往往流于街谈市谚之陋,有渔樵《欸乃》之不如者”[11],对此风气甚为排斥。也正是由于时人颇“以今乐府自鸣”,使杨维祯标举“古乐府”时具有了崇古与尊体的意味。
杨维祯对古乐府首重“古意”,要求其继承《诗经》的“风雅余韵”,具体而言,则是《诗大序》所代表的儒家诗教传统。对诗教的追求始于杨维祯从事古乐府写作之初。在《潇湘集序》中,杨维祯回顾与李孝光创作古乐府之初的经历,述及彼时自己的认识说:“梅一于酸,盐一于咸,饮食盐梅,而味常得于酸咸之外。此古诗人意也。后之得此意者,惟古乐府而已耳。”[12]这段关于古乐府诗体特性的体认之词常被研究者引用,但如何理解“饮食盐梅,而味常得于酸咸之外”却是难点。若仅将之视作“意在言外”之义,那古乐府又与其他诗体有何分别呢?其实,杨维祯在此序中对《潇湘集》作者唐升的评价,正可补充对“咸酸之外”的认识:“其乐府、古风谣,平易不迫,非有所托不著,至愤顽嫉恶,慷慨激烈者,闻之足以戒,而言之无罪矣。《三百篇》以六义见讽刺,潇湘诗人不合于古风人者寡矣。”[13] 杨氏所看重的,是将愤激慷慨的作者之志,寄于“平易不迫”的诗句之内,是以极淡泊之辞,蕴藉极充沛之意。因此,其“酸咸之外”不仅是从读者接受着眼的“言有尽而意无穷”,而更重要的是作者要将“所托”的“讽刺”之旨经过加工注入其中。这正是《诗大序》中“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14]的风教之旨。
杨维祯对古乐府中“诗教”的重视影响到吴复、章琬等“铁门”弟子,而他们又在编撰杨氏诗集时将此加以阐扬。如《铁崖先生古乐府》十卷由弟子吴复编辑,而吴氏于每卷之后的按语中几乎都会谈及此卷诗歌的诗教指向。在卷一之末,他说以上二十六首诗“或述古乐府旧事,或补古乐府所缺”,而“美刺存焉,劝戒彰焉,读者有所感发,则事父事君,而天伦无不厚矣”;卷五之诗多关于实事,吴氏则说“大而天变,细而民情,微几沉虑,寓于谲讽之中,闻之者可以戒,采之者可以观矣”;卷七诗作多托物言志,吴氏评价此卷“皆先生涉历世故,有概于衷,多托于鸟兽草木以起兴者。讽者得其旨,则劝善惩恶,盖亦不无补云”[15]。类似的阐发,俯拾皆是,而“美刺”“劝戒”“谲讽”等理念皆能从《诗大序》中找到渊源。章琬亦杨维祯得意弟子,他在《辑铁雅先生复古诗集序》中记载杨氏之语:“诗难,乐府为尤难。吾为古乐府,非特声谐金石,可劝可戒,使人惩创感发者有焉。”[16]若将此与张雨对杨诗“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17]的评价相比照,杨氏所自我标榜的,仍然是其“劝戒感发”的诗教追求。
方长安将古典诗教离析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前者以《诗经》为底本、以儒家的《诗经》思想为原则,后者则泛指任何以诗歌作品为底本、以礼义伦理为鹄的的教育行为。[18] 从杨维祯对古乐府的诗体认知来看,他的诗教正处于狭义与广义之间:他虽然以自己的诗作为中介,但他坚信古乐府是直接继承《诗经》品格的。杨维祯回顾弟子金信从游自己的经历说“首诵余古乐府二百,辄能游泳吾辞,以深求古风人之六义”[19],便流露出对自己古乐府的自信。当然,诗体认知与诗作之间总是会存在落差,杨维祯的古乐府也并不是每一首都有极强烈的诗教色彩,但诗教确实是其许多诗篇写作的直接动力。在杨氏诗中,孝子、节妇往往得到吟咏,古史今事都受到重新评骘,他也在许多诗序中表示该诗是为风教而作,这都是其诗体认知的具体实践。
古乐府若在诗教维度上继承《诗经》,其与《春秋》学之间的壁垒亦随之打通。在古典学术视域中,《诗》与《春秋》渊源密切,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20]这为后代谈论诗、史关系留下了无限阐释空间。杨维祯即对此解释说:“盖孔子录夷王、懿王之诗,迄于陈灵之事,而三纲五常有不忍言者矣。故《诗》亡《春秋》作。夫学《诗》者,诚未得于《诗》,又乌能得于《春秋》也哉!”[21]所谓“迄于陈灵之事”,当指《陈风·株林》。杨维祯认为,此时之诗已经是“三纲五常有不忍言者”,即不再能够“发情止义”、已经失落了诗教的功能;而孔子作《春秋》,便是以另一种形式承担起诗教之责,两部经书因此在情理上是一体的。这种同构性,被认为在杜甫身上得到了承续,杨氏《梧溪诗集序》便认为老杜之诗“其旨直而婉,其辞隐而见”,“非直纪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22]。杨维祯评论杜诗与《春秋》的相通性,即是在夫子自道:继承《三百篇》诗教传统的诗,是另一种形式的《春秋》。正是基于对诗教的体认,杨维祯将古乐府视作接续诗史传统的诗体。

杨维桢书《致理斋明府尺牍》
二
褒贬善恶:杨维祯的古乐府与《春秋》学知识
杨维祯所以形成强烈的诗教意识,与其深厚的《春秋》学素养关系甚深,《春秋》学知识也在其古乐府创作中或显或隐地发挥作用。从显性的知识上看,“君子原心”、重视“正统”等《春秋》学论点直接影响到杨氏古乐府的书写内容;而在隐性的知识上,主于“按断”的《春秋》学思维使杨维祯热衷于在诗中褒贬善恶,并显露出以此重构古史与现世价值的理想。知识与诗的杂糅,构成了理解“《春秋》之诗”命题的第二个层次。
杨维祯对《春秋》学的研治绵延一生,《春秋》学也几乎成了他的安身立命之基。杨维祯自幼从师攻习《春秋》,弱龄之前所熟悉的历代经说便“几逾百十家”[23]。延祐七年(1320),杨氏已年满二十五岁,而其父杨宏在铁崖山筑万卷楼,令维祯读书楼上,又“惧性弗颛易怠,去梯,辘轳传食”[24],如是苦读数年,贯穿经史百氏,终于泰定四年(1327)以《春秋》经登进士第。此后,他虽进入仕途,但屡次失官使他长期以主教席、课弟子为生,授《春秋》学于家乡诸暨、湖州东湖书院、松江府学等地,在其为弟子所作的记序之文中,提及“授之以《春秋》经史学”[25]之类的表述比比皆是。而宋濂所撰墓志铭称杨氏撰有《春秋透天关》[26],贝琼传状称杨氏撰有《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议》[27],杨氏则自己曾透露有《春秋定是录》《春秋胡氏传补正》《春秋合题著说》等书[28]。这些著作今已不存,但亦足见杨氏于《春秋》经学的用功之勤、用力之深了。
长期浸淫于《春秋》经学之中,使杨维祯在创作古乐府时常会引入《春秋》学知识。杨维祯治经不主于某一家,其所作《春秋定是录》即意在评议众说,这种取向与元代延祐复科以后,《春秋》经须用三传及胡安国《春秋传》的兼容并纳有关。[29]从其古乐府直接显露的《春秋》学知识来看,有两点尤其值得留意。
其一是“君子原心”,即讲求人物心迹,而不计现实其成败的是非观。“君子原心”来自《公羊传》,经董仲舒阐发,成为以《春秋》大义考量、体谅当事者本来动机的评判事实方法。[30]与此相对的,则是《左传》的某些事实判断,朱熹曾评论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31]杨维祯也说:“盖左氏之失,工于言而拙于理,好以成败论人、妖祥计事,往往传过于注。”[32]这种近于朱熹的表述,从反面显示出对“原心”的重视。咏史在杨氏古乐府中占有很大比重,其中往往发挥“原心”之说。譬如《蓝田玉》诗咏三国时吴将诸葛恪,诸葛恪曾有北上吞魏之志,但最终失败、壮志未酬,但杨维祯认同其“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古今未之有也”[33]的心迹,于是“予以《春秋》法原其心,不以成败祸福论恪,为赋《蓝田玉》以哀之”[34]。又如杨维祯古乐府中有《聂政篇》《易水歌》《失匕歌》等多篇题咏刺客之作,“议者谓传刺客非《春秋》旨,盖尝论刺客有义有不义辨”,但他认为为国报仇并非不义,故“吾取义烈于志,不计其功成与败也”[35]。研究者指出杨氏许多古乐府“具有动人心魄的悲剧美感”[36],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热衷题咏这些符合“大义”却现实失败的人物,其思想渊源即是“君子原心”。
其二是重视“正统”。《春秋》虽讲求“大一统”,但“正统论”进入《春秋》学讨论范畴主要是在宋代以后,这与朱熹编纂《资治通鉴纲目》有关。朱熹没有关于《春秋》的专门论著,但像揭傒斯说“《纲目》不得不继《春秋》而作”[37],朱右说朱熹“祖《春秋》以修《纲目》”[38],在元人看来,《纲目》一书便是朱子的《春秋》学著作。据载,朱门弟子曾问《纲目》主意,朱熹曰:“主在正统。”[39]从此,“正统论”也成为后世《春秋》学中的重要命题,杨维祯在谈论正统时即说:“臣维祯素读《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谓大一统之书。再观《纲目》之绍《春秋》,文公有‘在正统’之说。”[40]此时,《春秋》开篇的“王正月”已被视作重视“正统”之渊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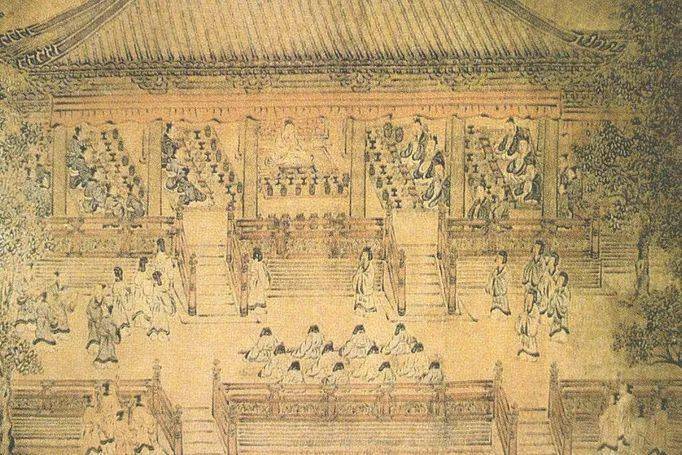
杨维祯本人特重“正统论”,他曾不满于元廷搁置修《辽》《金》《宋》三史时出现的正统问题,上《三史正统辨》;此后,他又有志“续为圣人麟笔之绝”,著《宋三百年纲目》推举宋之正统,隐然有建立“《春秋》—《通鉴纲目》—《宋三百年纲目》”序列关系的志愿。在正统论的命题中,三国时代的“蜀汉正统”是朱熹与朋辈子弟讨论甚多的话题,这也是其与司马公《通鉴》持论不同之处。[41]在古乐府里,杨维祯的《凤雏行》《赤兔儿》《猎许谣》《后梁父吟》等大量作品皆标举蜀汉正统,与朱熹之说相呼应。 此外,杨维祯以乐府诗所咏历代史事,上起三代,下迄于宋,而不及辽金史事,这本身也是一种正统论的立场,与其极为自信的《三史正统辨》相互表里。
在“君子原心”、重视“正统”等《春秋》学的具体知识之外, 杨维祯古乐府热衷褒贬评骘的特点更是受《春秋》学影响所致。《春秋》是褒贬之书,素称“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乃“王道之大者”[42]。杨维祯亦存在这种理想与自觉,因而借诗篇予古人以臧否。譬如他指斥范晔不孝不忠,故“为赋《樵薪母》,以代史诛”[43],可见他对自己诗歌功能的理解;再如《糟豝胛》斥责隋末军阀朱粲,又说“粲,兽人,不足诛也”[44]。所谓“诛”,即是《春秋》史笔的一种权力体现,是以贬笔诛古人于既死。而对于其所肯定的人物,亦毫不吝惜赞美,且常常与史评不同。像以《在山虎》赞美孔融,称“融之正气,其挫损贼操者多矣”,身死而益显其杰;以《大目奴》称颂文钦、文鸯矫诏虽有罪,但“讨贼则不失其正”。如是种种,不能尽道。这种道德评价又自然延伸至对时人的议论,如《铁崖先生古乐府》卷六之诗多取材于当时的义士、孤女、节妇、孝童、铁面御史、遗民故老等普通人,“皆歌咏一时忠臣烈士、贞女孝童、仁人隐士之遗事”,被吴复认为是“其激扬世教,岂小补哉”[45]。而其热衷褒贬议论,意欲“拨乱世反之正”的精神,正源自《春秋》学。
三
属词比事:古乐府的诗体特质与诗教表达
杨维祯重视诗的教化功能,并将《春秋》学知识熔铸于诗作之中,这使其古乐府具有鲜明的个人特征。同时,诗教是凭借“诗”发挥其教育陶化作用的,特定诗体自身的艺术特质会影响、制约其诗教表达。我们应该追问, 杨维祯的诗体选择与其诗教之间是否存在“形式—内容”层面的关联与契合?
在杨维祯的诗论中,“情性”是其有意揭橥的关键概念,这为理解其古乐府的诗体特质提供了入口。杨维祯认为“诗出情性”,他说:“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有各诗也。”[46]这虽然肯定了诗是情性的投射,但并不意味着其间没有高下之别,相反,他认为“人有面目骨骼,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47],可见情性的境界关系到诗之优劣。何种情性为上呢?杨维祯的《玉笥集叙》是为爱徒张宪所作,也是其陈述诗学主张、讲述“铁雅派”缘起的重要文献,在文中提及“情性”一词即有六次。他在文中议论诗史:
《三百篇》后有骚,骚之流有古乐府。《三百篇》本情性,一出于礼义。骚本情性,亦不离于忠。古乐府,《雅》之流,《风》之派也,情性近也。汉魏人本兴象,晋人本室度,情性尚未远也。南北人本体裁,本偶对声病,情性遂远矣。[48]
杨维祯认为《诗》、骚、古乐府皆本于情性,但南北朝诗已因格律而疏离了情性,可见诗的高下不仅见诸情性的“高度”,亦取决于其在诗中的“浓度”。在此序中,杨氏还说他与同道所作之古乐府,被黄溍、陈绎等翰苑名流认为“有古情性”,能够“补本朝诗人之缺”。这段材料反映了杨维祯的一种诗体观:诗对“情性”的表现程度是与其诗体形式相关联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理想的“古情性”需要古乐府体来实现,其诗教也由此得以达成。
从杨维祯的古乐府作品来看,古乐府诗体在“情性”的表现方面至少有“代言”与“叙事”两方面优长值得注意。代人立言是汉魏古乐府中的常见形式,它以特定的人物视角揣摩其心理、抒写其心态,借由想象令当事人进入言说空间。在杨维祯的古乐府中,代言就是直接表现书写对象“情性”的便利方式。如《铁崖先生古乐府》的首篇《履霜操》就是代周朝孝子伯奇而作。相传伯奇因后母的谗言而被父放逐,《履霜操》即是其自伤之辞,但杨维祯认为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版本不符合伯奇之心,于是重作。与早期版本中“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听谗言”[49]之类的怨诉不同,杨氏在新作中写“嗟儿天父兮天胡有偏,我不父顺兮父宁不儿怜”[50],其中充满怨而不怒、反求诸己的言语曲折。吴复和黄溍评论此诗时,都指出它与《诗经·凯风》中“母氏圣善,我无令人”的句意殊途同归,而《凯风》素有“婉词几谏,不显其亲之恶,可谓孝矣”[51]的美誉,这不正是诗教的“主文而谲谏”之旨吗?杨维祯认为,只有如此才符合伯奇的“情性”,并以此“情性”干预世教,这形成了他重作此诗的动机。
在古乐府中,杨维祯不仅代忠臣孝子言,也有代女子言的诗篇,其中许多是借其口诉说忠贞义烈。如其《古愤》诗是坚贞女子蒙冤后的独白,便被论者誉以“感慨悲愤,永为一代奇作”,“孤臣孽子,志有未伸者读之,可为涕下”[52]。烈女与“孤臣孽子”的感通之处也正在于诗中对“情性”的体贴与表达。代言使作者从内部进入、以典型人物表现理想的“古情性”,这种言说方式与格律是难以兼容的——格律将限制和规范典型人物的声音,并且消解其情性的“古意”。从杨维祯的诗教观来看,代言是古乐府表现“情性”的一种优势。
在代言之外,古乐府体长于叙事,其不受格律等体制的局限而能较自由地讲述事件,并在叙事过程中融入作者态度,以此传达古之“情性”。关于古乐府的叙事功能,古人对此已多有留意。[53]在杨维祯的古乐府中,以叙事体式展开的诗篇亦占据了大多数。其中较长者,如咏汉臣梁冀的《跋扈将军》、咏魏徵的《田舍翁》等诗可达二百字左右,而其中较短者则是他自命为“小乐府”的短诗,仅五言四句凡二十字。其中,杨维祯本人对“小乐府”尤为自负,他说:“至小乐府,二三子不能,惟吾能之,故五峰李著作推为咏史上手云。”[54]可见杨氏将“小乐府”视作自己独擅之体。
从他所自恃的“小乐府”体中,即可以发现在叙事中表现“情性”的两种策略。一种是寓“情性”于写作的对象,如《贞妇词》写楚昭王夫人贞姜守信而死的事,其事经过类似于“尾生抱柱”,诗曰:“皎日常持信,仓皇不改真。君王符不到,水长渐台倾。”诗歌叙事交代了前因后果,用词极为简单,而黄溍对此诗的六字评语很值得参考:“《春秋》直笔句律。”[55]当典型人物具备所谓的“古情性”时,将之直笔写出并有意强调其美行,本身即可视作一种纪念和推扬活动。与此相对, 对一些不合乎作者设定的义理之事,杨维祯在叙事时则要采取另一种“曲笔”的叙述策略,尽量在看似简略的叙事中寓以褒贬、传达言外之意。如其《烽燧曲》写“烽火戏诸侯”这一相传已久的事件:“闻道骊山下,西戎已结兵。美人方一笑,烽火不须惊。”[56]此诗前十字是从事实层面着笔,后十字则是转入诸侯的想象视角,虽然文字平易,但诗的讽刺却突显于字句之中。从读者的角度来看,由这种内含褒贬的叙事也可以感受诗人的“情性”之正,进而受到道德层面的教化。需要说明的是,对正、反两类事件的叙事策略也见于其篇制较长的古乐府中,以叙事来“寓褒贬”“见情性”是其古乐府的常见现象,只不过其“小乐府”体将之表现得更凝缩和警策而已。当然,若推究其源,这种以叙事传递诗教的体式选择仍与杨维祯的《春秋》学好尚存在莫大关系。

杨维桢像
杨维祯在表现“古情性”时发挥了古乐府长于代言和叙事的诗体特质,这使其诗教表达具有“诗史”式的调性。 杨维祯自称“铁史”,著有《史义拾遗》《历代史钺》等议论史事之作,“史义”“史钺”等题目显示他重视的仍是史事中的义理与教化。史与诗,皆是其演绎“大义”的载体,弟子称杨维祯许多诗作“以古风人之兴象,带太史氏之评裁,诗家自老杜以来之所稀有也”[57],便是意识到了其诗教表达的“诗史”色彩。这也构成了理解“《春秋》之诗”这一诗学批评的第三个层次。
四
结语
本文从杨维祯对古乐府的诗体认知、其古乐府中的《春秋》学渊源、古乐府的诗体特质等多个层面解读了“《春秋》之诗”的意涵。既往研究多关注其古乐府不拘格律、追求陌生化、表现个性的一面,这固然是杨维祯的一种面相,但“《春秋》之诗”的视角则为理解其创作提供了另一种门径。其实,杨维祯张扬个性和关心诗教的两重面相皆不能忽视,它们的胶着缠绕正显示出近世文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在一方面,宋代以后经义试士成为常态,元代延祐复科强化了经术在元后期的流布与浸渗,其时以《春秋》登第者尤多。[58]杨维祯在古乐府写作时体现出的《春秋》学思维、观念、知识,乃至强烈的诗教追求,都与当时士人形成的知识结构与文化生态有关。但是在另一方面,杨维祯的诗教也具有其个人性,他标榜源自《春秋》的善恶褒贬皆基于其个人对《春秋》的体会及演绎,又因利用了经学话语而将个人判断权威化。在塑造自我形象的《大人词》中,他自称“其身备万物,成《春秋》,故能后天身不老,挥斥八极隘九州”[59],视自身为《春秋》的现世代言者,其诗篇也因此常质疑前代成说、睥睨古人大儒,显露出文化权力在此时的下移。绾结而言,杨维祯古乐府中个性与世教之间的张力,也正代表了诗教传统在元末的新变。
(向上滑动查看注释)
[1] 如清人顾嗣立论元代诗史曰:“至正改元,人材辈出,标新领异,则廉夫为之雄,而元诗之变极矣!”参见(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44页。
[2] “文妖”之说,见(明)王彝:《王常宗集》卷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23页。
[3]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033页。另,杨维祯的名字有祯、桢两写,本文从孙小力之说写作“祯”。
[4] 既往研究中,留意到杨维祯古乐府与教化或《春秋》学关系的论著主要有武君《从“铁雅”到“铁崖”——杨维桢诗学的自我构建与他人重建》,《文艺研究》2020年第9期;丁放《杨维桢与元代后期诗学的新变》,《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但因为其探讨的主旨并不在于诗教,故对此皆未深究。本文将对此进行专门研讨。
[5] 郭丽《论古乐府的经典化过程》,《浙江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6] 孙尚勇《乐府通论》,中华书局,2020,第594页。
[7] 黄仁生《试论元末“古乐府”运动》,《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8] 黄仁生《铁雅诗派成员考》,《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
[9] 本文中使用的体制、语体、体式、体性等概念界定,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4页。
[10]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144页。
[11]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147页。
[12]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151页。
[13]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151页。
[14]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唐)陆德明音释,朱杰人、李慧玲整理《毛诗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16页。
[15] 以上卷末按语参见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6、171、226页。
[16]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3949页。
[17] 彭万隆点校《张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第486页。
[18] 方长安《中国诗教传统的现代转化及其当代传承》,《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19]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033页。
[20]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2,第300页。
[21]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248页。
[22]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036页。
[23] 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353页。
[24] 李鸣校点《贝琼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第11页。
[25]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127页。
[26] 黄灵庚编辑校点《宋濂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1354页。
[27] 李鸣校点《贝琼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第14页。
[28] 参见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005、3312、3540页。
[29]《元史》卷八十一,中华书局,1976,第2019页。
[30] 过常宝《“春秋决狱”:汉儒话语权力的构成和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31]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20,第2617~2618页。
[32]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002页。
[33] 《三国志》卷六十四,中书书局,1959,第1435~1436页。
[34]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508页。
[35]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1281页。
[36] 张晶《“铁崖体”:元代后期诗风的深刻变异》,《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2期。
[37] 鄢文龙笺注《揭傒斯全集笺注》,学苑出版社,2020,第362页。
[38]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0册,凤凰出版社,2004,第546页。
[39]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2020,第3215页。
[40]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3507页。
[41] 赵金刚《朱子的“正统论”》,《福建论坛》2016年第2期。
[42]《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59,第3297页。
[43]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532页。
[44]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558页。
[45]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05页。
[46]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016页。
[47]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014~2015页。
[48]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3111页。
[49]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第833页。
[50]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页。
[51] (宋)朱熹注,王华宝整理《诗集传》,凤凰出版社,2007,第23页。
[52]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112页。
[53] 参见王世冲《明清时期的汉乐府叙事批评》,《乐府学》2020年第二十二辑。
[54]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350页。
[55]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66页。
[56]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261页。
[57]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145页。
[58] 元末梁寅《送李行简序》即指出当时以《春秋》为业并登第者尤多,《春秋》被时人称作“大经”。参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49册,凤凰出版社,2004,第396页。
[59] 孙小力校笺《杨维祯全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84页。

作者简介

崔振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元明清文学。
出版信息:
文章发表于《乐府学》第二十六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3月。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微信号:zhanghuangguoxue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董京尘 谢琰
责任编辑:刘桐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