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陈原说,我们在今天看到的诗歌和诗人,只是徒有其表,是一个符号,是社会不同类别中的一种,甚至最终把诗歌变成一种技艺或技能。我们丧失了诗歌的精神,失去了诗人的荣耀和尊严, 诗人已经变成了诗歌的敌人。

陈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东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全国冶金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作品百万字。作品曾被《新华文摘》《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青年文摘》《小说选刊》等转载推荐。多篇作品被散文年鉴和年选收入。出版散文集五部《祖父是一粒粮食》《大地上的河流》《大地的语言》《在大地上走丢》《大地啊 我的胎盘和墓地》。其中散文集《祖父是一粒粮食》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96年卷。《大地的语言》入选文学鲁军文丛。曾在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高研班学习。获得十月文学奖等。
诗人已经变成了诗歌的敌人
陈 原
诗人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称号。最初,它几乎和神的使者一起降临,他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闪亮的几个古老标签。那是一些最早从语言里飞升的人,他们是洪荒年代文明的闪电,预示着神已经来到我们头顶的天空。让人类感到诗歌几乎不是从语言和凡人间诞生,而是来自灵的高处,是最空灵的声音,带着人类最古老的神示和语言,带着人类古老的智慧和激情,它几乎诞生在一切思想之前。因此诗歌甚至不是思想、情感、智慧的累积,更不是产生于其后,而是人类最初的思想、情感、智慧的原核。所以它是世间一切人类情愫和文明的先导和引领。这有世界各个地域和民族的最早的文字经典,几乎都是以诗歌的形式呈现为证。诗歌的降临,就像一座殿堂的降临,诗人和神灵在其居住。古老的诗歌发出的是人类最古老的先哲的声音,那时候,诗人几乎没有肉体,只有精神的高贵和缥缈。他们隔空传声,召唤着众生。他们神圣高迈,并以神圣高迈自尊。几千年来,诗歌精神作为最重要的人类精神,一直延展着文明的根脉。人类也几乎是以对神的虔诚来维护诗歌和诗人的荣耀和神圣。但我们也无情地看到,人类的发展史并不是诗歌发展的历史,诗歌精神像一种枯竭的资源在减弱它的脉动。直到今天,我们只是把诗歌精神供奉在殿堂里,以及少数有灵者的孱弱的心田里。
我们跨越千年,却走进了文化的泥淖和物质欲望构成的现实里。当喧哗与骚动的世界滚滚而来,诗音在今天却是如此孱弱。
诗歌的走向乃是人类发展的悲剧性必然,是人类回收灵魂,回归肉体的结果。我们降低了人类精神飞行的高度。这是文化的背面,也是很现实、很真实的一面。我们在今天看到的诗歌和诗人,只是徒有其表,是一个符号,是社会不同类别中的一种。甚至最终把诗歌变成一种技艺或技能。我们丧失了诗歌的精神,失去了诗人的荣耀和尊严。我们把诗歌变成蘑菇一样的菌类附着在他物身上,唯独没有诗歌的独立性。我们对古老的高蹈的诗歌精神没有敬畏,我们把诗歌当成人性的化妆品,当成生命的一种美容形式。今天的诗人和诗歌与它本来的内涵已经相去甚远。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成群的貌似诗人的人,他们穿越社会的各个层面,唯独不穿越诗歌。他们没有写作之前,只有写作之后——揣着粗劣的诗歌去寻找赞美和奖项。现在的诗人过于拥有才华,过于享受诗歌的虚名,但很多时候这样的才华是诗歌的敌人,因为他们的才华没有品格确立,没有精神来源。即这样的才华来路不明,是与现实厮混、苟且、要价的结果。他们自甘降低自己,却全然不知。这几乎是当代诗歌的劫数。这个时代已经无法忍受诗人独来独往的酒神精神,而诗人则以丑态百出为本领而炫耀。
我一直用回避诗人称号和荣耀的方式来保持自己对诗歌的不疲倦和敬畏,保持内心古老的清醒。我极其害怕把诗人作为一个集体和组织,害怕诗歌与现实的平行与妥协,害怕诗歌成为一种集体的思维方式。我已看到很多头顶桂冠的诗人变得慵懒、迟钝、麻木,他们看似群情激昂,实则是虚脱和乏力。他们深陷在狭隘的诗歌文本里,像写生活说明书。他们思想迟钝、精神囿圄,却依然在耕牛般写诗,诗歌几乎成为他们的绳索。无论那样的诗人怎样躁动,诗歌多么汹涌,但诗人和诗歌的关系却是已经死亡。他们天天寻找诗歌,诗歌却在天天躲避,这就是诗人与诗歌的疲累和尴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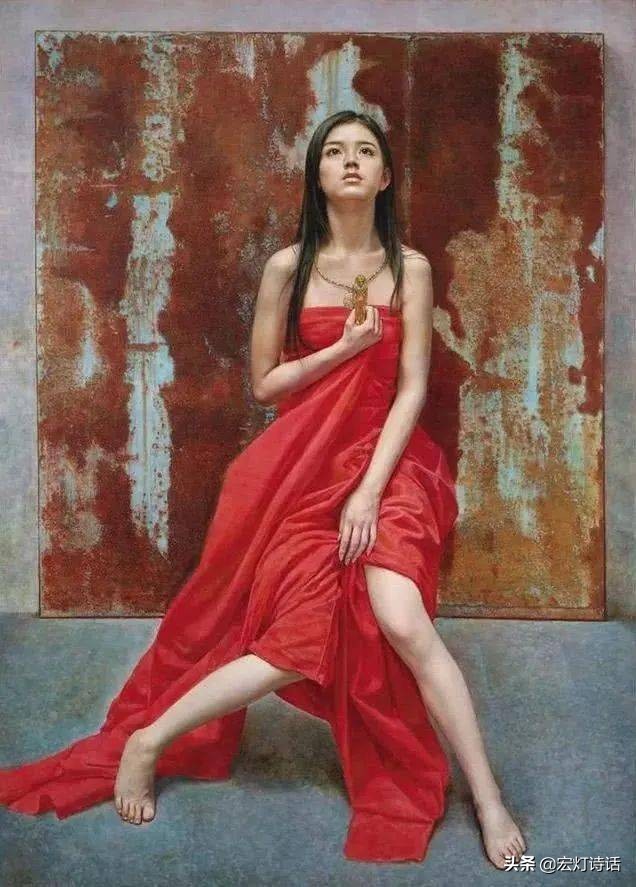
在当下重新确立诗歌地位,重新确立诗人与诗歌的关系,重新确立诗歌面对世界和现实的关系,以及诗歌和诗人的品质极其重要。诗歌的魂魄和诗人的魂魄,以及诗人的品质已经溃散,在今天,诗人只在自己的诗歌和生命内部晶莹强大。今天的诗人队伍有多大,诗歌的守墓者就有多少。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往往觉得没有诗歌,只有公众的分行与押韵。现在的诗人承受不住痛苦的力量。他们甚至学会了在诗歌里养生。他们甚至嘲笑诗歌对精神的承担,甘愿让诗歌坠入俗流。我坚信,如果没有新的诗歌格局和诗歌境界,诗歌只能是死亡得更漫长一些而已。
我迷恋诗歌这个最尊贵的容器,它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器皿崇拜。面对它,我常常内心庄重,超然于肉体的生命之上。但我从不敢炫耀我的高贵的金樽,他是我生命的私器,是我的生命密室。当眼前的世界和现实需要我们往前迅跑进入的时候,诗歌是我生命转向的地方,我和我的生命、我的灵魂通过一条隐秘甬道到达它。正如艾略特谈诗歌的时候说的,我们逃离公共性,并不是为了表达个性,而是追求更高的共性。
我背离着这个世界(当然更是背离着诗坛)已经写下了那么多的诗歌,这是我生命中很隐秘的一件事情。它们一直睡在我的肌体里,睡在我的灵魂里,我一直拥紧它们,获取生命的温暖和力量。它们的寂寞陪伴着我的寂寞。它们是巨烫的岩浆,而我是始终不肯喷涌的火山。我们藏在世界的一隅,自我照耀和构筑。我的诗歌买不起华丽的服装,它拒绝加冕。就像我自己。
其实从诗歌的角度,我从没有觉得有好或者不好的诗歌,我几乎没有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过它们。所以很多年,它们只在我的一个笔记本上,在我的一个文件夹里。当它渴望冲出更远的时候,我总是阻拦了它。我在乎的是,我使用了语言、韵律和节奏,表达了我内心的对世界的态度和体验,以及超验。
我不是诗人,一直不是,永远不是。我离古老的诗歌精神还很远。所以,我一直不敢过多地以诗歌的形式书写文字。但当我以其他文体写出文字的时候,很奇怪的是,我怎么那么喜欢使用句号?不仅仅是现在,很多年前的青春期的我尤甚。那时候,我曾经写过数篇不算长的,但整篇全是句号的文字。句号有终结感,不准备与人商榷,不怕也不在乎说错,不怕也不在乎断裂,反衬着我内心的一种刚愎自用和武断。句号是语言中最强的节奏。而不是简单的文字的分隔符。这一切正是诗歌的特性。我把虔诚的诗心装在其他的容器里。
建构生命里的诗性,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极其重要的。诗歌比思想更深刻更宏阔,比哲学更充满智慧和道理,比科学更科学,诗歌是深邃之上的感性与意象。诗歌是伟大的理性。是最大的哲学与美学。
但在当代,我们常常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汉语在当代押韵的频率,我相信一定是超过韵律时代的唐宋。你看看那些报告、总结、标语、口号、愿景、理想,以及各种段子和励志书,一排排、一片片押韵的句子,让我们感觉到了人的疯狂、浮躁、虚假。为了韵律,我们几乎不在乎世界的事实和真相。韵律成为我们掩盖错误的一种手段,成为时代虚假和浮漂的表征。
现在很多作家,当然包括所有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如果你拿掉他们所从事的创作部分,本人的思维和形态要么是个商人,要么是个政客,要么是个毫无内涵的空洞猥琐之人,他们的人本与文本完全脱离。作家的独立姿态基本完全丧失。他们与现实的同向,以及与生活泥潭的同沦,决定了他们作品的平庸与思想的干枯。更何谈诗歌精神的飞升?
我一直认为,为了到达文学的文学不是好的文学,至少不是有高度的文学。诗歌更是这样。只有那些进入哲学、美学、玄学、神秘学之后仍然不停止的诗歌,那些进入生命探寻与永恒的存在意义追问的诗歌,那些超越的诗歌才是大美的艺术。在这样的层面上,任何文学形式都不过是一种很低的可以借助的工具和器具而已。只有生命文本无限。
艺术的无限,以及生命的无限,以及一切存在意义的无限,将随着生命的有限而消失。并在另一个有限的生命的诞生里再生和延续。这应该是艺术和生命存在的绝对形式,也应该是一切事物和存在的绝对规律。
对于现在流行的诗歌写作,我们也许真的应该另立坐标体系和价值观。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正是当下写作生态的存在,是我想离开诗歌的唯一原因。我个人的力量只能做到:把诗歌当作我个体生命之内的事,而不是之外的事情。一己之力,只能如此。
真正的诗歌就是外化的另一种生命文本。生命结构是它的母本,世界的巨大内涵是它的母体。它的一切建构其实就是生命的建构,是生命内宇宙和生命外宇宙的巨大关系与巨大丰富性,是对这巨大关系、巨大丰富性的无限拓展与追问。
我越来越感到,越古老的事物越是有生命力。因此,即便孤独,我也要追寻古老的诗歌梦想,那里才拥有诗歌真正的尊严与荣光。
我喜欢一个伟大诗歌不断诞生的时代和世界。哪怕这个世界与我无关。
扬起头来吧,诗歌在高处。

延伸阅读:
大地是我的宗教
陈 原
广袤苍茫的大地,庄稼浩瀚的大地,亦黄亦绿的大地,一岁一枯的大地,在冬日的寒风中裸体的大地,馈赠给我们食物和水的大地,诞生我们生命的大地,埋藏我们肉体和骨灰的大地,……这就是我们的双眼看到的大地。我们的目光一遍遍掠过大地,并在这大地上寻找着。我想,这大地上肯定沉淀了许许多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在深深的泥土下面肯定埋藏着我们精神的根。基于此我常常感到自己的生命之树已和这精神的根相连接,所以每当我伫望大地,我就会有一种回望生命河床的感觉,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是那样愉悦、幸福、充实、庄严。大地永远存在于我的视野中。
但另一个现实是,在许多的人的视野中早已没有了大地。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城市和乡镇随着人类欲望的膨胀也在迅速地发达崛起。钢铁、合金、水泥铸就的一切事物占有了现代人的视野。人类的肉体得到了空前的享受。人如困鸟般躲在笼子般的房子里,肉体的满足已使许多的人不再关注精神,所以也就不再关注承载着古老精神的大地。人们食用的食物和蔬菜都是从机器上走下来的,人们几乎忘记了粮食和蔬菜本来的模样。更不用说大地了。人们已经不再对生命对精神进行内省,只在欲望的驱使里投机钻营、劳顿一生。难怪一位作家走进深圳后感触深刻地说,深圳没有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深圳不过是人民币的立体结构。——这令智者的目光多么痛苦。我一直在思索,活一个没有精神的皮囊,这就是人类追寻的生存目的?肉体和灵魂,欲望和精神,这是人类永恒的两面。天道难道注定了我们如果去追求就必须丧失——在对物的追求中丧失精神。那自苍茫的大地上诞生的以精神为内核的人类文明真的走到了极限?在这个世界上只剩下物质和被物质统治着的人。——这样的人还能称作人吗?我从来没有认为我们不应该追求物质,但是是否我们可以同时不失去承载着精神的大地?所以我禁不住再一次拷问,难道文明也是一种有害的东西?
这个时代需要警策。
大地作为一个综合的整体象征应该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可以恨它、诅咒它,甚至对它愤怒、对它咆哮,但我们不能遗忘它、抛弃它。是它诞生了我们,又是它收回了我们。我们失掉了水份就是泥土,我们和大地本来就是一体。而城市里没有生命的码头。城市只能麻醉我们消融我们,只有大地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是大地为了人类在不知疲倦地一遍遍地重复自己。面对大地我们应该感恩,应该虔诚,应该在心底里默默地朝圣。大地使人类踏实。大地是我们的宗教。
所以,当我某一天走进语言、走进艺术时,天性使我将生命最壮硕的那条根扎进了泥土。我一直苦苦地在大地上寻找意象,捕捉象征,探究我们生命的根据。我创作一篇文字,不过是用语言塑造一块土地,然后在上面耕种精神的庄稼。
我一直庆幸自己最初的生命诞生在大地上,诞生在大片的庄稼地中间的一个土炕上。那是鲁西一片一望无际的大平原,那里至今仍然是那么贫穷、封闭。人们毫无痛苦毫无欲望地自在地生存着。但如果抛却人类欲望的概念去评价,它无所谓贫穷和封闭。那里有我童年最圣洁的欢乐和幸福。我透明的影子摇摇晃晃在庄稼中间。我的先人们一辈又一辈地埋在它的下面,并为此更深刻了我对大地的情感。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奔波在归乡的路上,怀着一颗饱满庄严神圣的心和两行浊泪扑倒在故乡的泥土中。人生的风霜中我的心已逐渐地变得麻木坚硬起来,装成一个硬汉子生活在外面的世界里。但当我在故乡熟稔的土地上站立良久,我便会热泪涌流。是大地的沉默和安祥打动并激活了我的生命。我的泪水是那样任性、自在,毫无一丝文人的做作和矫情,那是真正的喜悦的圣灵的液体。在很长时间里我对大地的感悟局限在我对故乡的情怀里,也常常把故乡的大地当作大地这一整体意象的全部,但我逐渐地感到故乡大地的局限潜进了我的意识,并因此也局限了我的生命视野。那只是我个体生命站立的大地。所以我也一直在寻找着精神上的突破与超越。
时代毕竟在变化,故乡也在变化。我逐渐地感到故乡也在某种人类共有的欲望里急切地渴望和骚动着,并为此丧失了许多的朴实、诚笃的本质。它使我感到我一直在心中葆有的故乡的形象在变形在失真。我忆念中的故乡终于停留在一个时间的点上,不愿再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为此我曾写下这样的句子:我回到我的故乡,而故乡早已不知去了何方。我并不是责怪农人们追求物质的权力。他们那样贫穷,他们应该得到更富足的物质上的享受,但我总在担心他们会失去他们身上天然的被泥土塑造而成的精神本质。
……故乡已远去了。但这促使我去思索超越故乡之外的大地。如果说故乡只是我个体生命站立的大地的话,那么只有对故乡的超越才能使我真正进入人类共同站立的大地上。我的文字也才能有机会获得对人类命运进行关注的永恒视野。
这些年来,我以大地为稿笺,以生命情感为墨汁写下了几行被称为散文的东西,算作我对大地的一点回报和感恩。我期求以散文的手段实现对大地与生命关系的探究与揭示。也许散文承担不起如此大的命题和使命,但我能够做的只有这些。面对大地我有愧,但我微不足道,我的愧也微不足道。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文体什么的,我自然而率性的生命能成为什么样的文字就成为什么样的文字。我服从这样的天意。大地的结构就是我文字的结构,大地的意象就是我的语言,大地的品格就是我文字的品格。实际上那些有智性有悟性的人用不着读我的文字,他们应该去阅读大地。
在凝望阅读大地的人群中,我发现了老子、耶酥、米勒、海德格尔、费希特、鲁迅、歌德、托尔斯泰、张炜、莫言、韩少功、费孝通、苇岸……我们并不孤独。
大地永远是人类的背景。我透过自己的语言去凝望大地。

无限是宇宙的深度,也是灵魂的深度
陈 原
灵魂,就是把星空藏在心里,藏下一个与身体功能没有逻辑关系的无限广阔与无限可能。从而让有限的身体,充满无限的明确和无限的神秘。当我们抬起头,看到了天空,就看到了灵魂的颜色和质地,但它仅仅是灵魂的局部,而不是全部。无限没有全部。
不要以为天空在飘渺处,不要感叹宇宙是与我们无关的一种存在和无限。其实它和大地,和一切具象地呈现的万物在一起支撑着我们。任何一个具体的生命都是宇宙的中心,只是我们在丧失这个主体。我们每个具体生命的相遇与并存,都是一个具体生命和宇宙的综合体和另一个具体生命和宇宙的综合体的相遇与并存。宇宙必须是我们在独享之后,才能共享。
身体里藏下的无限与宇宙的无限是相同的。但我们可悲的是只去感知身体的有限,而不去感知这样的无限,以为我们从来不具有这样的无限。其实我们一直在无限里,而不是在有限里。有多少生命主体就有多少无限的宇宙和宇宙的无限。天空是有限的,但它只是宇宙的面孔,真正的无限,就是在终极里失去一切方向。
有了这样的宇宙的无限,就拥有了宇宙的万能目光,就像日月星空,并超越日月星空。我们是宇宙的原点,这不是宇宙的赋予而是灵魂的赋予。我们只有在原点才能感知到具体,除却原点我们只有无限,就像宇宙里的一切无限一样。灵魂的宇宙与无限不是物理法则决定的,而是一种感知与玄妙,是一种超越物理法则的宇宙的有机性和合理性。灵魂的难度是如何确定具体生命与宇宙的无限的结合,是一个具体的生命如何获得这样的无限,或者是我们是否知道去获得这样的宇宙的无限。因为我们感知的一切具象其实都是假象。为此我们要与宇宙结合,就必须绕过宇宙的表象,绕过它的呈现,就像绕过我们自己。那样的通达才会进入无限。
所以无限是宇宙的深度,也是灵魂的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