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女性的身体作为概念和物质的存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其中包含了太多文明进程中,给予女性身体的规训与惩罚。
在一次次的规训中,女性被训化为男权社会所需要的那个样子,其中不排除卖弄、谄媚、依附,以及视野的窄小和由身体自由的限制所带来的的思想的局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大批有着先锋思想的女性作家,在大量的女性文本里,探讨了女性身体和思想的觉醒之路,只是成果寥寥。铁凝的探讨,比较冷静,但也不乏充满残酷的性实验意图。比如《玫瑰门》和《麦秸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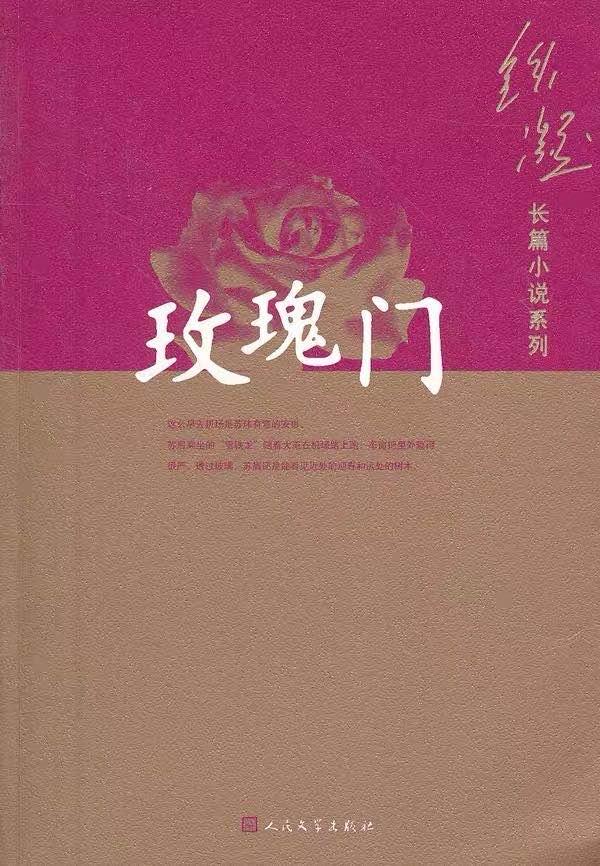
01
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体的理论最核心的问题是认识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是如何通过各种意识形态、话语和实践建构的。在西方社会,身体、性和社会性别是相互交织的。[1]布鲁克斯认为身体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暗示着xing,不仅是单纯的生殖性,而是复杂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欲望和禁忌。[2]
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的身体一直处于悬置的状态,它们被种种的男性话语、神话禁忌所架空。女性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禁言之物”,身体处于放逐的状态,因此,与身体息息相关的性以及社会性别的给予都处于一种未名状态。
所以,众多的女性主义者在为女性正名、为女性存在的呼喊中,都是从女性的身体着手:西苏说“写你自己,你的身体应该被人听到”。戴锦华认为,放逐了身体与欲望的书写,无疑同时放逐了女性主体的性别身份。[3]

因此,女性身体在女性解放自我、发掘自我的历史中,成为一种症候式的场域。通过对身体的感知,或者在接受自己身体的感觉信号时,女性才真正进入作为女性存在的时空当中。
02
在《玫瑰门》的叙事中,身体叙事成为焦点,在一系列的女性形象中,我们看到的是女性身体的被遮蔽、被误解、甚至鬼魅化,而这些构成了这些女性身体的悬置,悬置意味着缺失,即性本身的缺席。

在司漪纹的身上,我们几乎可以看见张爱玲《金锁记》里曹七巧的身影,性的受阻使她在苏眉的眼里成为一个乖戾的形象,性在她的世界里成为一种扭曲。她在内心偷窥儿媳儿子的生活,甚至嫉妒竹西那旺盛的欲望;又处心积虑地拆穿竹西与大旗的奸情,而这种拆穿只不过是她与罗大妈的一场较量,为的是让罗大妈“高抬贵手”,她甚至还遗憾自己让眉眉去当了那个捉奸的马前卒,但是“那分明就是她自己,她不过是让一个自己走在另一个自己的前边,然后让这一前一后的两个自己汇集在一起。”“她愿意四只眼睛共同看一个热闹”,但“司漪纹看见这个端坐在床前的竹西,心里不由得生出几分……几分怜悯之心吧,最真实的怜悯。”[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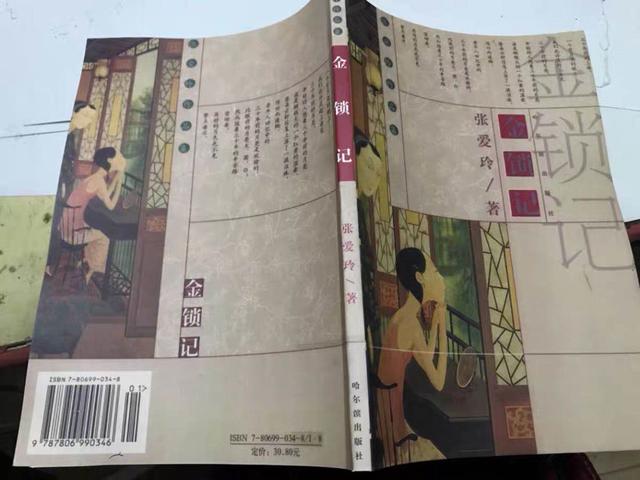
在这场较量中,我们看到司漪纹始终是处于怯弱的位置,她需要借助一个孩子来取消她内心的恐惧,在面对性时的恐惧。另一方面,她的对于竹西的怜悯是不是又是对自身的怜悯呢?庄绍俭对待她的身体的方式是扭曲的,更多的是一种侮辱性的讨伐,性成为一种丑陋的东西,因为她的身体是被玷污过的,是不干净的。
而她在半夜用妖娆的赤身裸体去恐吓庄老太爷,这就不仅仅只是一种报复,更多的则是一种对自己身体的理解:它尽管悬置,但依旧美丽,而且充满力量。这可能是司漪纹的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发现自己身体存在的时候,她发现它的力量,并用它开口说话。

03
正如西苏论述的,长期以来,妇女们都是用身体来回答迫害、亲姻组织的训化和一次次阉割她们的企图的。[5]这可能又是一种女体的歇斯底里,用这种超越道德的行为对身体被禁闭作出反抗。
然而,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用暴露身体来获得身体的问题,也不再是用暴露的身体来反抗传统道德的问题,她已经构成了女性身体的觉醒和强大的需要,只是面对需要,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在《玫瑰门》这个文本里,从司漪纹、姑爸到竹西到苏眉,它构成了三代女性不同的身体观念,也展现了女性在身体、性观念上的发展道路。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知道司漪纹在身体观念上是被异化的,她的偷窥、嫉妒等一系列行为只能证明她没有自己的身体。而姑爸的女扮男装和男性化行为直接就把作为女性的身体放逐了。到竹西这里,她明确地知道身体的要求,前后三个男人证明了她的挣扎,而挣扎确定了她身体的意识状态。只是最后,她也没有能够把身体安放在一个合适的地方。
对于年幼的苏眉而言,身体与性都是参杂着恐惧的,她的意识里是规避它们的,甚至逃离,她觉得“再也没有比一个女裸体直面另一个更残忍的现象了,那是一种寒冷的悲愤,一种尖酸的尴尬。……在那时我以为我永远不能被任何人看,爱情和身体和身体的暴露有什么关系?”[6]直至成年,直至分娩,她才想她那样应该最像《赤脚医生手册》里的那张图了。她也才真正从身体本能的紧张恐惧里获得一点坦然、一点安心:
“她想,也许丑不是一个女人直面过世界的这块老荒地,而是你认为这荒地丑”。[7]
这里可能已经达成了对身体与性的释然,就像她觉得产后的缝合是庄严的一样。
04
而在《麦秸垛》里,我们一样感受到了女性的那种身体被悬置的状态。“麦秸垛”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为性的禁忌的象征。

按弗洛伊德的说法,禁忌是能够被明显地意识到的……禁忌和本能共存:就本能而言,这是因为它只是被压抑并未消除;就禁忌而言,如果它停止了,本能又会强行回到意识并进入到实际的行动中。[8]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阐释“麦秸垛”这个意象呢?它是性的暗喻的同时,又在文本里充当了禁忌的角色。而禁忌之下,必有欲望。[9]
也就是说,“麦秸垛”是作为一个矛盾体存在的,是身体与性是否能够打破禁忌而获得实现,实现后又当怎样的隐喻。可以说《麦秸垛》是铁凝的一个直接进行性发问的文本,这里可能涉及性别权利和两性关系处理的问题,但它的实验姿态是无疑的:女性在走出身体解放这一步后,到底能获得什么呢?
沈小凤这个形象或许能给出答案,她的积极主动的性姿态,最后是失败的。她的失败,在我看来是女性争取身体自由的失败;她的失踪,成为一个悬疑,或者意味着女性身体的最终悬置,它的主动姿态没有获得外界环境的认同。尽管她获得了一次性,但这个获得比起杨青的自我束缚更具悲剧性。
它成了“在”而“不在”的“在场”,这种“在”是被剥夺的“在”,是实实在在的被缺席。
05
而杨青更多的是在大芝娘那里获得一些女性的体认。大芝娘丰硕的xiongpu能让她腿上生出许多劲来,这看起来有点荒唐的表述,实际却是在那个无名时代,个体获得的一个外界参照物。
知青是没有性别的,杨青对于大芝娘xiongpu特殊的感觉,正是因为她从中有了一种身体的实在感。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杨青身体的被悬置,她对沈小凤的报复,也证实了她对沈小凤获得xing的嫉妒。
无论《玫瑰门》还是《麦秸垛》,其中的身体的状态,似乎都可以用反复出现的大芝娘那空悬的丰硕的胸脯来作一个阐释性的隐喻。
rufang,是女性的第二性征,是哺育的象征,随着文明的发展,它又掺进了性的成分。丰硕的rufang,无论是作为哺育还是作为性观看的对象,它都是具有不容置疑的成熟性的。
而《麦秸垛》,作者把它们放置在一个寂寞的视角里,观照着女性的身体,而仅仅是放置,并没有让它们获得实实在在的归宿,这也是女性写作一直想要突破的地方,却总是不得力,更有甚者,反而进入了一种适得其反的尴尬境地。

关于乳房的描述,不得不想起莫言的《丰乳肥臀》,只是,在那高密乡里,这又是另一种男性视角下的女性身体呈现,主动与被动,都只是男性视野里的揣测而已。
本文节选于作者《寂寞的文本》一文,首发于《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此文节选有删改。
参考文献:
[1] 苏红军.《身体》[A].《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Z]. 柏棣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8页.
[2](美)彼得·布鲁克斯.《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M]. 朱生坚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7页.
[3]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4] [6] [7] 铁凝.《玫瑰门》[M]. 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411页,第267页,第515页,第405-406页.
[5] (法)埃莱娜·西苏.《杜美莎的笑声》[A].《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Z]. 张京媛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202页.
[8] [9] 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A]. 邵迎生译.《弗洛伊德文集》[C],第五卷. 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第31页,第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