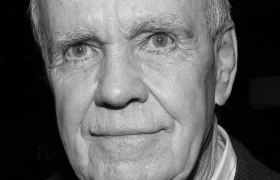喜欢王安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王安忆是以“日常生活”为通道,将“个人经验”与历史、现实相沟通而佳作的。
王安忆力图挖掘出日常生活的内在性,在她看来,日常生活具有一种韧劲的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默默地穿越时代的关隘,保持自己的特色。
李敬泽在评论小说时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如果一定要谈论‘标准’,那么我相信,一个最基本的可以通约的艺术标准就是‘细节’。”王安忆的日常叙事中,都淡化故事情节,而以细节结构小说。
大量地铺陈细节也是王安忆叙述语言的一个特点,细节成了小说的眼睛和灵魂。王安忆用细节来阐述市民的日常生活,使得寻常小事具有诗意美。
王安忆在城市题材的小说中有意回避了现实社会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这样的创作取向决定于她独特的历史观:“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她认为小说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
王安忆多年来的创作,致力于发现市民日常生活中,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在思考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女性往往是她问题意识的载体。
一、《流逝》中的端丽:在劳动中,发现生活的趣味与诗意
在她的作品中找不到任何宏大叙事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精致乖巧的老虎天窗,晒台上随风飘浮的衣服等等,一幅声色各异的弄堂生活画卷徐徐展开。
《流逝》写于1982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欧阳端丽轻视劳动,而且雇用了保姆和奶妈来帮她料理家务、照看孩子。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端丽和她的家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不仅失去了过去的财富、地位、休闲和舒适的生活方式,并不断被社会贬低、轻视。

作为家里的长房儿媳,端丽迫不得已撑起了家庭的重负,她在运动中逐渐被夺走金钱、时间以及自由。她不得不走出家门,走向职业领域。欧阳端丽从一个“雇主”下降为“雇员”,从一个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变成看护孩子的保姆以及工厂间女工。她辞掉了佣人和奶妈,自己担负起家庭劳动的全部任务。

好逸恶劳是多数人的本性,端丽在“文革”中的劳动是不得已而为之,正是这种“被迫”的劳动带领她重新发现、审视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在充当保姆照顾孩子庆庆的时候,身为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她第一次感受到当妈的酸甜苦辣;家庭的经济越来越困难,端丽的劳动也从私人领域转向公共领域,她进入街道工厂,在“绕线圈”这一简单、乏味的手工劳动中,她发现集体劳动的趣味,“同大家一起笑”令她觉得有趣,很开心;将自己过去的旗袍成功地改成女儿的衬衫带给她很大的成就感;她甚至觉得节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还发现了红烧肉烧蛋这种“粗糙饭食”的美味。
在这十年间,端丽重新发现生活的趣味与诗意,而正是这种趣味和诗意在很大程度上支撑她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过去从未尝试过的体力劳动,在劳动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尊感,实现了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超越。

在小说结束时,文化大革命也结束了,一切似乎重新回到了原点,但这十年的岁月在小女儿咪咪身上已经刻下鲜明的痕迹,从小苦惯了的咪咪问端丽,“不工作,过日子有什么意思?”

而端丽思考的是十年的辛苦,岂能轻易取消其意义,“总该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吧!”
这篇发表于1982年的作品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潮流的映衬下极为特殊: 它不止于控诉历史带给人的创伤,而是力求从所谓的“创伤”中寻觅向上的、超越自我的精神能量, 为这“十年”重新赋予意义。
二 《长恨歌》里的王琦瑶:改头换面,靠劳动养活自己
《长恨歌》写于1996,是获奖最多的作品。同样是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入手,它通过写主人公王琦瑶的一生来演绎一个城市的历史命运。在另一些小说文本中,文革处处充满了暴力、危机、紧张和异化,但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在文革中照样有滋有味地过日子,把生活打点得很精致。
《长恨歌》讲述了上海小姐王琦瑶的一生沉浮。王琦瑶虽然完整地经历了中国50年来的风云变幻,但是王安忆避免从正面直接触及这个历史话题,在这个作品中,她只谈日用、饮食男女。

历史的沧桑都浸透在普通人的生活起居当中,王安忆只从茶点、衣着、摆设、娱乐的小处着眼,将一部城市的大历史讲得踏实妥帖、切肤彻骨、充盈四溢。
在王安忆笔下,1948年的春天,不是乱世风烟,而是爱丽思公寓的寂静;1957年的冬天,不是你死我活的“反右”运动,而是革命时代对日常生活的谨慎享受:“屋里有一炉火,是什么样的良辰美景啊!他们都很会动脑筋,在炉子边上做出许多文章。烤朝鲜鱼干,烤年糕片,坐一个开水锅涮羊肉,下面条。”
在小说的第一部,王安忆极尽其所能铺陈了一个旖旎、精致的四十年代老上海,将少女时代的王琦瑶的虚荣和欲望写得百转千回。
在物质诱惑面前,王琦瑶似乎选择了一条“自甘堕落” 的路,心甘情愿地做军政要员李主任的外室。然而王琦瑶并非头脑简单的金丝雀,她对自己的命运其实有着清晰的了解和体察:当她身披白色的婚纱站在流光溢彩的康乃馨雨中闪亮登场的时候,她其实已经意识到自己早已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也许穿上婚服就是一场空,婚服其实是丧服”当她第一次走进爱丽丝公寓这个美丽的牢笼, 舞台上的预言瞬间成为谶语,“……她婚服倒是穿了两次,一次在片场,二次在决赛的舞台,可真正该穿婚服了,却没有穿。”片场和舞台上“假”的美艳更反衬出真实世界中真正的冷酷。
随着李主任的死和国民党政府的倒台,王琦瑶貌似伶人般光艳动人、实则千疮百孔的前半生彻底宣告结束。 自苏州邬桥归来的王琦瑶改头换面,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护士,用职业支撑起低调、简朴又独立自足的生活,而且以一己之力养大私生女薇薇。
 过去的岁月始终如同阴影一般笼罩着王琦瑶的生活,但她自始至终都在努力摆脱一个“旧我”:她不再是仰仗男性权力、金钱的毫无主体性的弱女子,而是勇于为自己负责的、具有主体性的人。
过去的岁月始终如同阴影一般笼罩着王琦瑶的生活,但她自始至终都在努力摆脱一个“旧我”:她不再是仰仗男性权力、金钱的毫无主体性的弱女子,而是勇于为自己负责的、具有主体性的人。在由王琦瑶、严家师母、康明逊等人的小天地里,唯有王琦瑶是依靠职业、劳动养活自己的。
在五六十年代的时代氛围中,王琦瑶用自己的劳动构建起平常的生活,一度超越了自己不光彩的前半生。此外,在王琦瑶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几个男人的恋爱中,她的爱情其实远比与之相对应的男子更加勇敢、饱满,爱情支持她更加勇敢地生活下去, 带领她通往更加丰富的可能性。
泡沫般的四十年代留给王琦瑶的是一首长恨悲歌, 是五六十年代的市民生活方式,将王琦瑶从旧梦中解脱出来,开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些蛰居狭小、浅陋的弄堂,不问世事、只管柴米油盐的平民女性直面人生的独立、坚忍的精神之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正是王安忆所展现出来的女性独特的景观。
三 《富萍》中的富萍:在最底层的野菊花,终有春天
写于2001年的《富萍》是王安忆颇为得意的作品, “甚至比《长恨歌》还满意”。小说呈现出一种迥异于《长恨歌》 的上海五六十年代的生活:从扬州乡下来到上海投奔奶奶的富萍先后经历了淮海路、苏州河、梅家桥三个城市空间,最终被梅家桥的精神感召,在梅家桥安顿了自我。

在《富萍》的文学想象中,梅家桥是一片单纯、健康、仁义的土地,在这里,贫穷的生活培养起了美好的品德。这部小说中,作家置上海的繁华于不顾,把笔触伸向上海这座大城市的底层——一个由形形色色的外来打工者所构成的城市底层民间,用还原生活常态的朴实与本真来征服读者。
富萍只是想拒绝别人已经安排好的生活,逃离别人的操控,过自己能够独立自主的日子,这就是富萍生活和婚姻的目的。富萍以她特有的韧性在城里默默生活着,她与一个以糊纸盒为生的跛脚青年走到了一起,找到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归宿和立脚点,靠自己的双手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我们是野菊花,我们在最底层、最贫瘠的土地上奋力昂起头。我们努力拔高自己。尽管我们微不足道,然而我们终究是一个生命。”富萍内心的坚韧,她身上具有的那种女性特有的打不散、折不断的杂草精神,可以说是王安忆小说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意识的核心。
王安忆对生命意识有着独到的见解:处于边缘的人们面对艰辛生活不懈追求和努力,表现出来的韧性的进取力量和态度,显示出生命个体的底色。

人在生命追求中,由于自身的原因和处在他乡的陌生环境中,必然会产生孤独感和漂泊感;爱情是生命的本来存在,成为新世纪女性凡俗生活的调剂品。
四 《桃之夭夭》中的郁晓秋:救人救己的“市井观音”
在写于2003年的长篇小说《桃之夭夭》中,王安忆致力于塑造一个“市井观音”的形象,并把诚挚的赞美慷慨地献给郁晓秋:我个人对她是寄予希望的。她是在一种在粗鲁的爱中成长的女孩,我想把她塑造成“市井观音”,救人救己。
其实家庭中看不起她的哥哥姐姐,过得还不如她,她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人,可以救自己,最后还救了别人,当然这种救赎都是不自觉的。

郁晓秋是一个从晦暗中成长起来的阳光女孩,尽管“传奇”的身世和“过分”青春洋溢的美丽的身体带给她不计其数的误解、流言甚至耳光,但她还是在市井的注视下健康、活泼地长大了。
倘若根据儿童发展心理学来预测郁晓秋成年的性格,难得出她长大后将会形成诸如顽固、冷漠、残忍或怯懦、盲从等性格这一结论甚至罹患抑郁症,但郁晓秋突破了“心理学”的预测,拥有了比在正常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更健康、更完善的人格。
她超越了成长的痛苦,最后不但拯救了自己,也拯救了两个濒临破碎的家庭。做姐夫的续弦,照顾起一家老小的生活,似乎多多少少有一点“献身”的意味,但郁晓秋的个人魅力和叙述者的慈悲心肠最终让她和姐夫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朴实、真挚的感情。

在青春的尽头,这个善良的女子以纯粹的利他行为,不经意间收获了自己的幸福。郁晓秋来自上海的市井中,“拥簇杂芜的市民堆里产生流言,可是这流言又不至于太伤人,市井有着约束道德的作用,同时却又有许多开放的空隙,这些因素都对郁晓秋的健康成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五十到七十年代的上海市井哺育了郁晓秋,郁晓秋这一“市井观音” 的形象使她成为一个宽容、慈悲并富有生活智慧的女子,最终渡己渡人。
王安忆的作品背后,隐含的是人道的温情,让人去感受生命的欢乐与忧伤,是对女性生命意识的别样歌唱。
总结
“每一日都是柴米油盐、勤勤恳恳地过着,没一点非分之想,猛然间一回头,却成了传奇。上海的传奇均是这样的。传奇中人度的也是平常日月,还须格外地将这日月夯得结实,才可有心力体力演绎变故。”王安忆回忆。
与其说王安忆对世俗生活充满热爱,不如说她真正热爱的是世俗生活背后所隐藏着的平凡人的智慧和生命力。正如王安忆自己所说:“持久的日常生活就是劳动、生活、一日三餐,还有许多乐趣,这里体现出来的坚韧性,反映了人性的美德。”
王安忆理解市井人们的生活,欣赏市民精神的力量,她的小说描写着世俗生活的琐事,却流淌出一种“温暖”和“饱满”的生命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