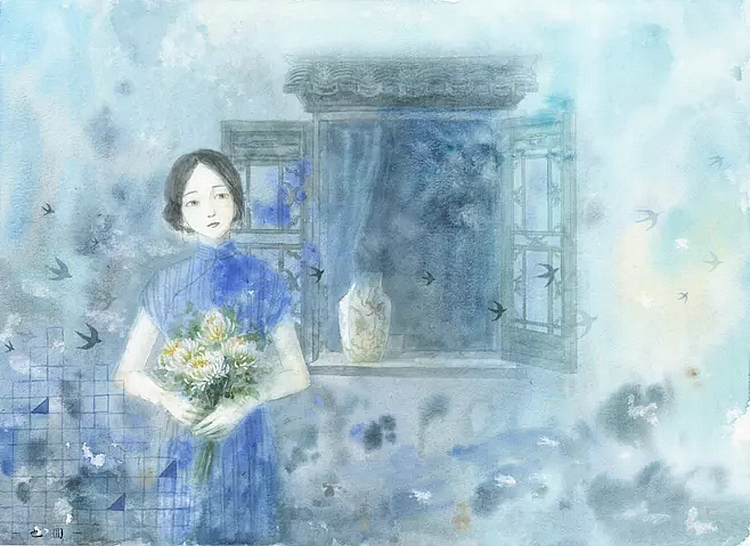
上世纪
我赌博输掉古敏华的第二天,韦春龙从监狱里出来。他像一头从磨坊里脱逃的公牛,在广阔的天底下奔跑。四年的囚禁或劳役使他迷失了方向。他站在一条笔直的公路上,找不着北。他望着公路的一头,心想前面如果是北的话,那么后面就是南。这样他将拦住从前方开来的车。但如果前面是南呢?甚至是西?晕头转向的韦春龙手脚盲动。他像一只笨重的陀螺缭乱地旋转。东西南北在他心目中像容貌相似的四胞胎难以分辨。最后他决定哪辆车先开过来,不管是往东还是往西、往北还是往南,他都要把它拦住。
韦春龙抵达南宁的时候,我输掉古敏华算起来已经四个月了。这四个月的时间里,一些事情的发生不可避免,它们就像厨房里的鸡鸭必然挨宰一样不出所料。
首先,我被迫把古敏华许给了陈国富。她就像某弱国的一座美丽岛屿在一次不平等的谈判后割让给了对之觊觎或侵占已久的强敌一样,从一种生活制度变成另一种生活制度,从祖国的版图上消失而在侵占国的版图上出现——
陈国富,你狠。古敏华现在是你的了。你们爱怎样就怎样,我不管了。我对翻出三张A和一对Q的陈国富说。
五张红黑和数目分明的扑克牌像一份庄严缜密的文告摆放或出示在陈国富胸前的桌面上,相比之下我胸前桌面上的五张牌逊色、弱小,像一封轻浮松散的书信。我的牌势比不过陈国富的牌势,就是说我的运气不如陈国富的运气好。他三张A带一对Q,而我是一对K、一对5和一张J。我斗不过陈国富,就是说我输了。愿赌服输,那么我就得把古敏华许给他,因为古敏华是我的赌注和筹码。我没有钱了。我口袋里的三万块钱全没有了,它们是我干了许多个日日夜夜挣来的,却在一夜之间输了个精光。它们像一军血气方刚的战士,被我亲手送上前线,去和陈国富等人的兵团作战。然后我眼睁睁看着它们一营一营、一团一团地被陈国富等俘虏和吃掉。它们在残酷无情的战场上全部叛变投敌。
天快亮的时候,我已身无分文,像一个光杆司令。这时候赌桌边只剩下三个人:陈国富、梁迪和我。其他的人都走了。吴宏一大概是凌晨走的,他老婆见他那时候还不回家,就猛呼他,况且那时候他正赢着钱。赢着钱的吴宏一当然懂得怕老婆,他一副坐立不安和心烦意乱的样子,不再继续下注。田平见他谨慎保守的阵势,知道从他身上夺回损失已没有希望,就说你走吧,你走了说不定我运气会好起来。吴宏一一听,像小学生听到老师喊下课或放学似的,拔腿就走。他走后,田平真的时来运转,连连得手。半夜三更,他点了点回收到口袋里的钱,一边点一边喘气。点完,他说不打了。再打下去我的心脏受不了。梁迪说屌,赢了钱都想走。田平说我赢什么钱?他拍了拍装钱的袋子,我带了两万块钱来,现在也是两万,打平。梁迪说打平你不会走的。田平说我就是打平,不信你可以点。梁迪说好好好,你打平,打平。田平说我主要是心脏受不了,再打下去我肯定会心肌梗死。梁迪说我输了那么多,早就心肌梗死了。田平说你和我不同,我有心脏病,而你没有。你就是有心脏病,输多少也不会有事,因为你有钱。梁迪说以后我赢钱,也说自己有心脏病。田平说骗你我不姓田。他掏出一个药瓶,说这是地奥心血康,你看!陈国富这时候说让他走吧。以后我们要规定时间,比如说三点,到三点谁想走就可以走。我说输的可以提前走,赢的到规定时间才能走。梁迪说输了谁想走,你现在想走吗?陈国富说别怄了,现在是我赢,我陪你们玩到天亮,行了吧?你们不就是想从我口袋里捞钱吗?我给你们机会。田平捂着胸口站起来,说那我告辞了。没人愿意搭理他。他离开了赌桌。
田平出门时顺便把门关上的声音吵醒了伏在我肩膀后昏睡的古敏华。她撑着我的腰把头抬起,慵懒地说还赌呀,都什么时候了?我说别吱声,睡你的。古敏华说还要赌到什么时候?我说天亮。古敏华说哎哟,那我不难受死了?我说谁叫你来?叫你不来,你偏要来。到沙发上去睡吧。陈国富立刻说这哪成,到床上去睡。古敏华说你没听见让我睡沙发呀?我不耐烦地说去吧去吧,你想上床上去睡就去吧。古敏华说那我去睡了。哥,你小心点,别输光了。我突然怒狠狠地说你嘴巴怎么这么臭?古敏华顿悟她说了赌徒忌讳说的话,吓得便跑了。
我妹妹古敏华去了陈国富的床上睡觉。我、陈国富和梁迪又继续赌。那时候我只剩下不到一万元钱,另外的两万元已像鲜肉被如狼似虎的吴宏一、陈国富他们生吞活剥。他们不仅吞我的钱,还吞梁迪的。梁迪说他带了五万块钱来,现在只剩下不到五千了,这群鳄鱼!他酸楚地说。陈国富说输了你不能怪别人,只能怨自己倒霉。梁迪说我会要你吐出来的。陈国富说那么来吧。
我们三人用摸牌的方式重新选定座位。我摸到的牌最大,于是我指定坐陈国富原先的位子。陈国富居第二,坐到梁迪的位子上。我原先的位子,非梁迪莫属,但是他不乐意。他说我申请坐刚才田平的位子行吗?陈国富说可以。我说随你便。我们像部队换防或士兵换岗一样在新位子上坐定。又一轮战斗打响。
不到一个小时,梁迪屡屡受挫,剩下的五千块钱,像国民党留在大陆企图颠覆新生政权或幻想复辟的涣散兵匪,很快就被清剿殆尽。他再也没有力量或资本赌。而我所剩无几的资本也像负隅顽抗的小股武装一样苟延残喘,危在旦夕。满脸沮丧的梁迪像一个痛失金牌而含恨从竞技场退下来的运动员,无心观战。但是他叫我顶住。他又像一个难得糊涂的教练一样,明知道大势已去或败局已定,也要鼓励队员拼搏到底。古天明,他直呼我的名字,坚持住,天无绝人之路。陈国富说对。林彪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而毛主席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时候你要相信毛主席的话,别听林彪的。陈国富的话煽起我的欲火。我说陈国富,你下注吧。陈国富说我只能下两千了,因为你只有两千。他把两千压在牌桌上,我把两千扔出去。
这一扔扔尽了我的所有,像拿最后一个肉包子打狗一样。我垂头丧气地靠在椅子上,像一只自投罗网或在劫难逃的食肉动物,在食肉的捕食者的陷阱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陈国富掂了掂膨胀爆满的一口袋现钱,然后顾视我和梁迪,说你们知道你们输在哪儿吗?不等我们回答,他就说你们输就输在位子上。上半夜你们的位子不好,但下半夜运气转到你们的位子上,你们又换了。尤其是古天明,你不该和我换位。我说我才不信这个邪。陈国富说那还赌不赌?我说没有钱了,拿什么赌?陈国富说你虽然没有钱了,但是你还有古敏华。我说去你妈的,你不是人我还是人。陈国富说有话好好说,骂人不能解决问题。我说我宁可拿我的命做赌注,也不拿古敏华做赌注。陈国富说你的命值个屁钱,我才不要你的命。我只要古敏华。我说你做梦吧你,长期以来你勾引我妹妹我还没警告你。陈国富说我喜欢你妹妹,真心喜欢。你妹妹也喜欢我。我赢钱她比我还高兴,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希望你不反对古敏华嫁给我。我说不行。陈国富说我们再赌一把,我拿三万块钱,你拿古敏华。我输了,对古敏华死心,三万块钱还让你拿走。我赢了,你同意古敏华嫁给我。怎么样?我说不行。陈国富说五万?我摇头。七万?陈国富涨价。我还是摇头。陈国富说十万,行了吧?我说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梁迪就说干吧,十万块钱还不干?你赢了,没话说,天意。万一你不赢,也是天意,说明古敏华该嫁给陈国富。陈国富说其实我除了离过婚这点缺憾外,有哪方面配不上你妹妹?我说你就是有几个钱,还有什么?陈国富说这就够了。我心一横,说操,你以为你准赢吗?你赢不了。陈国富说那来吧。他收拾起扑克牌,利索地整理。那唰啦啦翻动的扑克牌像钞票在点钞机上运转一样。然后他把扑克牌递给梁迪,说你来发牌吧。
梁迪即将发牌的时候,我说去把古敏华叫出来吧,万一怎么样,她要愿意才行。陈国富说这个你放心,如果她不愿意,就算我赢了,我决不勉强她。现在的问题是你。我说那好,来吧。
我输了。
古敏华从陈国富的床上起来后,我对她说敏华,哥哥全输光了,连你也输进去了。古敏华揉着惺忪的睡眼,说你把我输给谁了?我说陈国富。古敏华说是吗?她的眼睛忽然清澈透亮,睡意一扫而光。我说从现在开始,你解放了,爱跟谁跟谁,我不管了。
古敏华说是真的吗?
我说是真的。
古敏华喜出望外,像一个已被判处徒刑的人犯忽然被改判无罪释放一样。她扑进陈国富怀里。
韦春龙从监狱出来,一百多天才到达南宁。他像一只蜗牛或乌龟,慢慢地缩短和我们这座城市的距离。从他开始拦第一辆车到那辆满载山羊的汽车出现,没有任何一辆车肯为他停下来。他的招手像乞丐的跪拜毫无作用。事实上,乞丐的跪拜时不时还引人驻足停留,偶尔还有零碎的钱币投在浅薄的碗里。但是韦春龙的待遇不如乞丐。后来他终于觉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他。他光秃秃的脑袋和灰溜溜的囚服像一堆硬屎和一团皱纸,使洁身自好或明哲保身的人们见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
那辆满载山羊的汽车开过来的时候,韦春龙已藏在树后。他像一只懂得人性的猴子一样对人隐避。他从树后盯着愈来愈近的汽车。当车头从树前一过,他蹿了出来,纵身一跃,抓住了车厢尾部的栏杆,然后蹬足。他的跳跃飞快轻巧,使车头的人无所察觉,像一只飞蚁落在腾动的马屁股上。
韦春龙脚跟未稳,他看见了山羊。密集的山羊被围困在车厢里,像难民营里的难民。韦春龙钻进车厢,成为一只山羊。
山羊们为韦春龙让开或挤出了一块地方,它们就像公共汽车上为老弱病残让座的优秀乘客一样,使韦春龙能够坐下来。他感动地看着默默为他奉献的羊群,像多年以前他看见银幕上数以百计的民众为保护一名干部的安全而舍生忘死、惨遭迫害。
汽车像一名马拉松运动员,在公路上长跑。它从遥远的山区出发,说不定来自我的家乡上岭村,然后经过了无数的村庄和城镇,终于抵达它的目的地。它跑进一个杀气腾腾的地方,那是一个屠宰场。它的大门像虎口,吃进一汽车山羊后立即关闭。韦春龙看见长着利牙的铁门封锁了出路。他来不及跳车脱逃。
几个手上沾满鲜血的屠夫把韦春龙像拽猪一样拽下来。因为他不像山羊一样有角,他们就揪住了他的耳朵和肢体,还有一个人在后面踢他的屁股。那些一路上与韦春龙唇齿相依的山羊已一只接一只被拽下车。它们的稀疏和减少使韦春龙无法藏匿,身体暴露。
一阵拳打脚踢之后,韦春龙才有解释说明的机会。一个一手插在裤袋一手拿着手机的男人来到他的跟前。韦春龙开始向这个男人解释。他说对不起,我错了, 不该爬车。但是我爬车不是想干坏事。我只是想回家。他一说话,从鼻孔里流出来的血就从他嘴巴里进去。我是个劳改犯,他继续坦白地说,但是已经得到释放。是提前释放的,因为我表现好。我在监狱里只待了四年,而判的是五年。我有证明。韦春龙从内衣的口袋里掏出证明,还有一百元钱。钱是夹在证明里,连带着出来的。他索性都递过去:我补票,这是监狱发给我的路费,我补票。拿手机的男人抽出裤袋里的那只手接过证明和钱。他看了后说,刚出狱就犯事,你胆子不小呀?韦春龙说我承认我错了,老板,我补票。老板说补票?没这么简单!你弄死了我几只羊,知道吗?他的手机指着车厢:你看看!韦春龙没有转头去看车厢,因为他知道里面有几只死羊。它们不是我弄死的!他申辩道,我上车之前它们就死了。它们是被闷死的。老板说是被你闷死的。你要赔,不赔就别想从这里出去。韦春龙说我赔,一百块钱全给你。老板一听就笑,说你在监狱里才待多久?一只羊现在值多少钱?装蒜还是怎的?韦春龙说可是它们真不是我弄死的呀。老板说你还抵赖!他的手机快点到韦春龙的额头上。我宰了你!他说。不,不,我不宰你,我把你送去当地派出所,说你劫车,让你再进监狱。韦春龙说我认了,等我回到家把钱寄给你。老板说你以为我是傻子呀?韦春龙说我把释放证押在你这儿。老板说不行。韦春龙说那怎么办?老板说你留在这里给我干活。按一只羊五百块算,四只羊就是两千块。你至少得干满四个月。韦春龙说好,我干。老板说你答应得这么干脆,我知道你想跑。我警告你别跑,释放证在我这儿,我不怕你跑。韦春龙说我不跑。
做了一段时间副手后,韦春龙拿起屠刀。第一只死在他刀口下的是一只生病的山羊。韦春龙敢杀它是因为看中了这只羊的软弱。它被连拖带抬架在一张长条凳上的时候居然不反抗和挣扎。一直劝韦春龙开杀戒的兰焕德说这只羊你再不杀,我就报告老板说你偷懒,让他叫你干五个月。他把屠刀交给韦春龙,像一名长官把武器发给新兵一样。韦春龙拿刀在手,像士兵被推上前线一样站到羊的前头。他扎好马步,单手抓住羊角,然后把刀尖抵在羊的咽喉。用身手在压制羊的兰焕德说对,就这样,用力捅下去,然后扭转一下刀柄,再拔出来。韦春龙在捅刀之前,看了一下羊的眼睛。他发现羊的眼睛阴冷哀伤,像无可救药的绝望病人,指望在医生的帮助下安乐地死去。韦春龙这才下了狠心,用力一捅。锐利的刀刺进羊的咽喉,只剩下刀柄在外。他依照兰焕德的指教,扭转刀柄,才把刀拔出来。鲜红的血迅速从豁口喷出来,像石油从井口喷射一样。一只塑料大盆在两步以外接着热乎乎的羊血,像酒店里的锅头,在为食客煮汤。
没过多久,韦春龙已和其他屠夫一样,手法熟练,技高胆大。他像是他们的高徒,很快学会和掌握了屠宰牲畜的技术。在这个私人的屠宰场,所有的宰杀,都是人工。刀便成为宰杀牲畜的主要工具。那些肥嫩的牛羊和猪狗,在韦春龙的刀下像农场的庄稼被收割得干净利落。
屠宰场的老板姓宋,叫宋桂生,但他的名字没人敢叫。韦春龙当然也不会叫他宋桂生。这天韦春龙见到宋桂生。他在心里骂日你妈的宋桂生!但是他嘴里却说宋老板,我求你,能不能现在放我出去?我已经在你这儿干了三个月了,而且我是很卖力地干的。宋桂生说不行,我这里又不是监狱,表现好就可以减刑,提前出去。我是做生意的,说四个月就是四个月。韦春龙摆头,说你看,我的头发都像羊胡子一样长了,你让我去理个发吧。宋桂生说你又想跑。韦春龙说要跑我早就跑了。再说我身上没有钱,释放证又在你手里扣着,南宁离这里还那么远,我怎么会跑呢?宋桂生说那就干够四个月。待在我这里总比你关在监狱里强吧?餐餐有肉吃,而且你又学会了一门技术。
当韦春龙在与我们相距二百公里的另一座城市屠宰牲畜的时候,我妹妹古敏华做了新娘。她像一个生怕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一样,迫不及待嫁给了陈国富。而事实上,我妹妹古敏华如花似玉,年龄只有二十三岁。如果不是年轻貌美,陈国富怎么会娶她呢?就像如果陈国富没有钱,我妹妹又怎么会嫁给他一样。陈国富是离过两次婚的男人。两次离婚分别在他富了之前和富了之后,或者说一次是老婆抛弃他,另一次是他抛弃了老婆。他的婚姻像一部导不好拍不完的戏,扮演女一号的演员一再更换,不是演员觉得认错导演拂袖而去,就是导演觉得选错演员好生辞退,于是又选新的演员从头开始。那么我妹妹古敏华就像是被选定的女演员,怀着纯真而远大的梦想,进入导演的剧组,和导演上床。
婚后不几天,陈国富把那天我赌博输掉的钱如数退给我。他一手抓钱一手揽着蜜月里的妻子,说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怎么好意思要你的钱。我说这是你劳动所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常言道赌桌上无父子,何况我们的关系比父子隔得远着呢。愿赌服输,这点赌德我还是有。陈国富说不行,我必须退给你。古敏华说哥,拿去吧,本来这就是你的。我一边接钱一边说这好像没道理,钱本来是我的,这么多,没错,但是我已经输掉了,怎么又是我的了呢?古敏华说怎么没道理?这就好像我本来是你妹妹,现在我嫁给他做妻子了,但我还是你的妹妹呀。陈国富马上说好!他兴味盎然地看着他怀里的女人,像收藏家欣赏自己的一幅藏画。
几万元赌资回到手上,我当然高兴,就像失窃的财物回归原主肯定会让原主喜出望外一样。
我决定和朋友乐一乐。
在南宁我其实就几个朋友:陈国富、韦春龙、吴宏一、田平和梁迪。陈国富成为妹夫后不能算了,韦春龙在坐牢,那么就剩下吴宏一、田平和梁迪了。
我先给田平打电话,说今晚我请客。田平说赢啦?我说鸟,一定要赢才请?你什么时候见我赢过?田平说我以为我不在的时候,你又和他们干。我刚出差回来。我说算为你洗尘。田平说还有谁?我说梁迪。田平说吴宏一呢?我说算了,他那个老婆管得严,要叫你叫。田平说我叫他,另外,我可能还带一个人去。我说带吧。他说什么地方?我说富龙城,就是上次你请客的那个地方,六点。
接着,我找梁迪。先打他手机,竟然关机。而他平常是不关机的,除了还在赌博和做爱以外。我想梁迪肯定不在赌博,而是在做爱。那么这个时候和他做爱的必定不是他老婆。为了证实我的判断,我往他家打电话。我知道他老婆在家,因为他老婆是我们医院的护士,上的全是夜班。电话只“嘟——”响一下,我就听到了他老婆的声音。我说小钟吗?我是古天明。今晚我想请梁迪吃饭,他在吗?小钟说他不在,你打他手机吧。我说好的。然后我又把电话打到梁迪的公司。我知道他不在公司,因为他从不坐班,但我还是多此一举。接电话的是一位小姐。我说你好,请找梁副经理。小姐说梁副经理不在,请你打他手机吧。我说好的。
于是,只有呼他一条路了。我通过人工台呼他。我对呼台小姐说请呼8181508,我姓古。
打完呼机,我心里想我等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总该完事了吧?
我等了半个小时,我的呼机响了。我的呼机显示出梁迪的手机号码。我打他的手机,一拨就通。古大夫吗?梁迪开口先说,我知道他这么称呼我,其实是说给身边的人听的。于是我模仿他的口吻,说梁先生吗?梁迪说古大夫,你好呀。我说你在哪儿呀?梁迪说外面啦。我说你在外面干什么呀?梁迪说我跑业务啦。我说跑什么业务呀?梁迪说当然是公司的业务啦。我说我知道是什么业务啦。梁迪说找我有什么事吗?我终止调侃的语气,说请你吃饭。梁迪说你也想出国吗?我说富龙城,你来不来?梁迪说新加坡,好呀,那里的医院最需要像你这样的大夫啦。我说六点。梁迪说好,这事我一定给你办。马上。
六点,我准时等来田平。他带着一个陌生的秀气女子。这女子就像一种我不知名的花朵,把像瘦木一样的田平衬出些许阳气。田平先向这个女子介绍我,他说我的朋友古天明,第一人民医院主治医师。竺竺,他说出女子的名字,女诗人,文坛新秀。梁迪呢?他紧接着说。我说还没来。他说吴宏一说要晚一个小时到。
话音刚落,吴宏一到了。他匆匆忙忙、脚步生风,一到来就说,为了吃这顿饭,我把最后一节课给停了。学校离市区太他妈远了。我说为了你重视友情而不讲师德的行为,我再点一个好菜。吴宏一说田平说今晚喝茅台,我是冲茅台来的。我说没问题。我招呼一旁的服务员,说你听见这位先生讲的酒了吗?
然后田平对面面相觑的竺竺和吴宏一说,等梁迪到了,我一并介绍。
十几分钟后,我们等来了梁迪。他只身一人,一脸惬意的神情。我说出国手续给人办完了?梁迪一笑。田平说这次去多少人?我说你看他那表情,一副吃饱饭的样子,少不了。吴宏一说这里面有没有我的学生?梁迪说一般般,可有可无。
然后,田平对竺竺、吴宏一和梁迪相互介绍。他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先介绍竺竺:竺竺,女诗人,文坛新秀。然后他指吴宏一:吴宏一,桂邕大学青年才俊,中文系讲师。最后介绍梁迪:梁迪,国际劳务输出及人才交流公司副经理。
三个被介绍的人互相致意。竺竺说吴老师,你好,以后请多多关照。梁经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吴宏一说有田平关照你,我就放心了。梁迪说女作家长得漂亮的,还真少见。
服务员,上菜!我插嘴说道。
我们坐在富龙城酒店食客满堂的大厅里,像一个好逸恶劳的小团伙,接受侍者殷勤的服务。我们吃上我们点的酒菜,扯着滞留在肚子里的话。几日不见,如隔三秋,谁都有话要说。田平说天明,我出差去了,没能参加你妹妹的婚礼,不介意吧?我说跟我无关,介什么意?她的婚礼,我都没有参加。田平说可能吗?我说是不可能,但是……梁迪说古天明在婚宴上待得不久就走了。我看见他走的。吴宏一说我证明,他心绞痛。田平说何必这样?生米都已经煮成熟饭了。我说吃饱喝足就走,这有什么?田平说你这种态度不好。梁迪说要有个过程,慢慢接受。吴宏一说强扭的瓜也有甜的,何况我看不像强扭。竺竺这时候看着田平,用会说话的眼睛问为什么?田平说他妹妹嫁了个大款。我看见竺竺奇异的眼神像一道雨天的彩虹。我说不谈这个,喝酒!我端起装茅台酒的酒杯。田平端起酒杯。竺竺端起酒杯。吴宏一和梁迪端起酒杯。几个酒杯碰在一起,像一簇飘香的花。
四男一女共同干杯之后,四个男人又连干了几杯。田平的脑袋从耳朵红到脸,像一个成熟的苹果挂在树上。竺竺就问他还行不行?田平说没事。吴宏一说田平的红脸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看起来不得劲,其实是得的。梁迪说田平,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田平说东奔西跑,组稿呗。出版社今年经济指标划到个人,重得像苛捐杂税,员工累得没个人样。我应该取个名字叫东西才对,可惜田代琳已经抢先一步叫东西了。吴宏一说那你在东西前面加个狗字呗,和正宗的东西有个区别。梁迪说再重再累也压不倒你,你能耐大,张贤亮的稿子你都能组到。田平抬手做了个赶的动作,说嗨,现在谁还组张贤亮的稿子?不组啦。梁迪说名作家的稿你不组,组谁?田平说演员、节目主持人。梁迪一愣,说演员、节目主持人,他们也……会写作?田平说哎,这些人一写起书来,一出版,不光作家,什么家的书统统都得往后靠,摆一边去,大折价!梁迪说我操,如此说来,写作天才全藏在影视或娱乐圈里,只要他们一动笔头,全惊天地、泣鬼神?
吴宏一就说梁迪,这你就不懂了。你以为演员、节目主持人写书是为了当作家?你以为出版社出演员、节目主持人的书是以为他们是写作天才?你以为他们的书要有艺术性和思想性才能畅销?你以为读者读他们的书是为了欣赏文笔和接受教育?他瞪着梁迪,就像你,你以为你千方百计把别人弄出国去,是为了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而不是为了牟利?
吴宏一连串的“你以为”,把梁迪弄得莫名其妙又尴尬,说我问的是田平,又没有问你。
田平说吴宏一问得没错,我来回答。他顿了顿,夹起一块鸟肉咬后咽下,说隐私。隐私懂吗?广大观众想了解他们熟悉或者喜欢、崇拜的演员、节目主持人的内心世界、幕后生活,实际上就是想要窥探隐私。当观众看到写明星的书尤其是亲自撰写或口述的书,你说能不买来看一看吗?那么这样具有广阔市场和长远前景的选题或书稿,出版社能不开发吗?就像现在发现山中有金矿,哪能不挖?难道现在有哪个出版社不想赚钱?所以演员、节目主持人等这些大众偶像的隐秘世界或私人生活,可都是金子啊!隐私,归根结底就是这个,懂了没有?
梁迪说我懂了。
田平又说,至于吴宏一反问你的最后一个问题,你自己来回答。
梁迪笑笑说我拒绝回答。
竺竺闪着清纯的眼睛说我不太懂,一个人怎么能把隐私暴露给别人看呢?这多不好意思,谁愿意呀?我们是普通人都不愿意,明星们难道愿意吗?
田平说用钱买呀,你说他们愿不愿意?十万不愿意,就二十万。二十万不愿意,四十万、五十万。
梁迪说我操,值那么多吗?谁给我两千元我保证就把我的隐私卖了。
田平说你?你的隐私除了你老婆想知道以外,谁都不想知道。这主要是看谁。名人不同呀,名气越大,隐私就越值钱。×××那本还没写呢,就先炒,抬到一百〇八万,愿意了吧?卖了吧?这人我想你们各位是知道的。
我们都表示知道。
另外一些大名鼎鼎的演员、节目主持人,要价也不低啊。田平又吃了一块鸟肉后说。或一次买断,或吃版税,都是狮子大开口。我数几个给你们听。田平说着举起一只巴掌,五根手指像树木竖在我们眼前。××× 、 ×× 、×××、×× 、××。田平每说一个名字,就扳下一根手指,像伐倒一棵树。我看见五棵树全倒下了,田平的手掌变成拳头,像光秃秃的山峦。然后他举起另一块巴掌,继续细数,×××、×××、××、×××。最后,只剩下一棵树不倒。它残留在山上,像一个坚守阵地的英雄。田平抬举他保留的一根拇指说,都是这个呀。他的这根拇指,像是表示夸奖,又像是表示数目。就是这样,我们搞出版的,还互相打抢,田平说,争先恐后,害怕抢不到。我这次出差,就是去打抢呀。抢到了吗?梁迪问。我的眼睛也在问。
抢到了,田平说,不过只是签了协议。稿子还没拿到,正在写。
吴宏一说你信协议这东西呀?稿子没拿到,什么都是空的、假的,就像你不把女人明媒正娶抬进家里,你就不敢说她是你老婆。
田平说但是订金已经付了呀。订金已经付了。
多少?我和梁迪问。
三十万。这只是一半,田平说,交稿时付另一半。
你去哪儿弄这么多订金?
筹呀,田平说,出版社垫一部分,我借一部分。
说老半天,这人到底是谁呀?这又是我和梁迪共同的问题。
×××,田平说,你们应该懂得的啦,他演过什么电影你们可能记不得,但他是谁的前情人,哪个不懂?×××,号称中国影后的前情人啊!我这么一说,你们就知道这书有写头,出版后有看头,作者和出版者更有赚头了啦!
那这书将来出版了,你能拿多少呢?我说。
田平说反正以后我看见你妹夫陈国富,不会再感到很自卑就是。
一百万,六十万,梁迪摇头,表示不可思议。通奸不付费,奸情抵万金,风流不作罢,还过出书瘾。梁迪信口吟出一首五言绝句。
竺竺扑哧一笑。
我举手,说我有个问题,问田平。
田平说你问。
我说既然现在作家不吃香了,演员、节目主持人吃香,我看了看田平身边还痴笑的竺竺,那么你为什么还和作家形影不离呢?
我看见竺竺的脸唰地变得绯红,我和田老师只是普通关系,她说。我说我知道,看出来了,目前是。竺竺的脸还是红的,她说我有男朋友的。我说田平还有老婆呢。
竺竺说我见过师母,她很漂亮。
吴宏一说你的意思是说家猫一旦养尊处优或锦衣玉食,就不会在外面偷腥了?
竺竺说田老师才不是那种人。
梁迪说我了解田老师,对田老师最有发言权,他一不偷二不抢,守株待兔,等女人投怀送抱,愿者上钩。
竺竺的脸变黑了,被我们几个毒辣的话抹的。
田平敲了一下桌子,说你们几个能不能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是个出版人,虽然逐利,但依然是有情怀的,对好作家的好作品,还是要出,赔本也要出。他转而对生气的竺竺,说等×××的书出版赚了钱,我就帮你把诗集给出了。
竺竺的脸又开朗起来。
我们又来了兴味。新鲜的欢快,是开始表演的模特掀起的。她们像一群下凡的天使,披挂着用森林的树枝、树叶编成的裙子,向着广大的食客走来。她们走过食客身边,在像石林一样的桌椅间绕来绕去。她们用性感的嘴唇、乳房、臀部和大腿吸引食客的目光,使食客放下筷子、杯子,停止进食,就像鸟用生动美丽的翅膀、羽毛和鸣啭,使猛兽目瞪口呆一样。她们越来越裸露地走着,像流水洗涤山丘和风卷残云,使食客轻浮的时间和金钱得到消耗和消遣。
我前妻把儿子从幼儿园骗走的那天,我遇见韦春龙。
我去派出所报案,而韦春龙去派出所报到。我们的重逢像戏剧中的巧合。
我从派出所的门走进,而他则从派出所的门走出。我们像两部进出关卡的车子,迎面相撞。
韦春龙?
古天明?
我们彼此称呼对方,带着疑问,尽管我们明知既不会认错人,也不会叫错名字。尽管我们隔了四年多不见。我们的疑问是事情怎么会这么巧?
于是我认为,我儿子在这一天被前妻骗走,是上天或命运的有意安排,用意或目的是让我与韦春龙重逢,而不是为了使我失去儿子,就像我和陈国富的那场赌博,最终目的不是要我输钱,而是迫使我同意古敏华嫁给陈国富。
我来派出所报到,韦春龙说,我被放出来了。
好,我说。我没有马上告诉韦春龙我为什么来派出所。你等一会儿,我说,我进去一下就出来。
在派出所值班室,我对值班的警察说我的儿子不见了。值班警察说你的儿子为什么不见了?我说他被我的前妻骗走了。值班警察放下手中的报纸,说既然你都知道你儿子被谁骗走了,为什么还来报案?我说我和前妻离婚的时候,儿子判给我。如今她擅自把儿子要走,就是侵犯了我的合法权益。所以我来派出所报案,请求帮助,把我儿子追回来。值班警察说你前妻把儿子带去哪里?我说深圳。她现在带着儿子正在去深圳的路上。值班警察说这事你应该上法院,不该来派出所。我说为什么?值班警察说因为我们职责有限,或力不能及,就像人生病就应该上医院诊治而仅向单位报告是不起多大作用一样。我不明白值班警察所说的话,但是我说我明白了。我立马告辞,因为我知道韦春龙在派出所门外等我,他似乎比我儿子更牵动我的心。
我拉着韦春龙的手,像明目的人拉着盲人,在车水马龙的街市行走。他被动地跟着我,任由我牵引。他先是跟着我进商店,从上至下,当即换上我为他购买的衣服和鞋袜。再跟我进发廊,洗发剪发。然后我们进酒楼。
春龙,你受苦了,我说。这时候我和韦春龙是在酒楼里。吃喝的过程中,我们彼此把分隔后的经历告诉对方。一千多个日子,像一百两粮酿成一斤烈酒,浓缩成一个小时,高度地概括和表达。我们彼此沉浸在对方的经历中。我感受着韦春龙的痛苦和磨难。感念他没有出卖我,使我免于牢狱之灾。吃药品供应商的回扣,我也是有份的,科室的其他人也有份,但最后都是韦春龙一个人扛了。他感受着我的放浪和迷乱。我们动荡肺腑地吸纳和倾吐,像酩酊大醉的酒徒。
春龙,我又说,从现在开始,我要你好好生活。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为你找份好工作。
谢谢,韦春龙说,工作我自己找好了。
什么工作?
我打算去屠宰场应聘,当一名屠夫。等条件成熟,我自己开一家屠宰场。
为什么?我诧异地看着这名前大夫说。哪怕你去私人诊所应聘也行呀!
我喜欢上了屠宰,韦春龙说,我觉得当一名屠夫比当大夫强。
那……你现在直接开一家屠宰场,行不行?
我现在资金不够。
我给你筹,我们这帮朋友一起帮你筹。
谢谢,我以为时隔了这么些年,你们已经不再把我当朋友了。
你永远是我们的朋友,我说。
田平还好吗?韦春龙说。
好,我说,他像狐狸一样刁钻狡猾灵活精明。眼下正在策划出版明星的书,快发了。
梁迪呢,也好吧?
是的,我说,他现在是公司的副经理了,源源不断地送人出国旅游和务工,像野猫一样逍遥快活。
吴宏一怎么样?
他还是讲师,始终评不上副教授。
你离婚之后,又物色上新对象没有?
没有。其实独身挺好的。
川萍又嫁人了吗?韦春龙说。川萍是我的前妻。
嫁了。
嫁给谁?
一个港佬,但住在深圳。
真好,韦春龙说。他举起酒杯,邀请我和他干杯。
接下来,我想韦春龙该问及古敏华了。因为装在他心里的几个人,我知道还有古敏华没说出来。她埋在韦春龙的心底,像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
我等着韦春龙问及古敏华,像在劫难逃的人等着终结的子弹射向自己。但是韦春龙就是不问。
古敏华,她嫁人了。我忍不住说,嫁给了一个有钱人,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我没有拦住。
是吗?韦春龙说。他努力地举起酒杯。抖动的酒杯刚举到额眉却很快搁下来,像运动员抓举的杠铃没有举过头顶就从手里失落一样。
春龙,对不起,我说。
……
作者简介
凡一平,原名樊一平,1964年生,广西都安人。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跪下》《顺口溜》《上岭村的谋杀》《蝉声唱》等七部,小说集《撒谎的村庄》等六部,散文集《掘地三尺》等,作品获得百花文学奖、广西文艺铜鼓奖等,小说《寻枪》《理发师》《跪下》《最后的子弹》等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