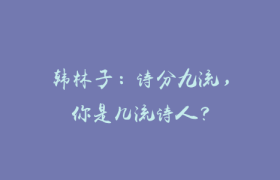编者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当代的新诗创作如何彰显美学品格和艺术追求,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当前广受关注的重要课题。为此,本刊特约请多位文艺评论家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创作与评论等多个层面展开讨论。
内容摘要:“新诗”最鲜明的特点是它的时代性,既是中国现代转型的产物,也主动介入了现代转型的进程和现代意识形态的塑造。这种介入体现了想象立场的改变和诗歌功能的调整,带来了题材、主题、语言策略的一系列变化。由于社会转型的内忧外患,中国现代诗人介入时代的方式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诗人,更加多元和丰富。转型社会人们会接受不同介入方式的诗歌,但更期待有内在表现力的作品,希望诗人能够用本民族的语言感觉和想象世界,用语言之光照亮时代现实中晦暗不明和难以言说的部分,为之找到恰当的言说形式和韵律。诗人介入时代,不仅是道德上的时代担当,也是接受思想与言说能力的考验。
关 键 词:新诗 时代性 内在介入 文化担当
“新诗”是一个名词还是动宾词?是一种革新诗歌运动还是一种诗歌类型?在学术上存在着不同看法,需要返回历史语境认真分辨。无须分辨的是,从初期的“新派诗”“新体诗”“白话诗”“尝试诗”,到1919年10月胡适写出《谈新诗》一文,“新诗”一词开始号令天下,主要是时代的因素。不仅因为它被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所催生,而且它自身也以感时忧国的姿态主动介入时代,参与了时代意识形态和一代诗风的塑造。这就是为什么,艾青的《中国新诗六十年》开宗明义:“中国新诗是时代的产物。中国新诗是为了适应中国现代社会变革而产生的,是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伟大变化的文学样式。”[1]

艾青
“新诗”时代性的直接体现,是题材、主题与表现形式的时代感。许多文学史著作叙述20世纪中国诗歌,谈论“新诗”运动的起点,不谈胡适1916年写的《答梅觐庄——白话诗》与发表在《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发行)上的《白话诗八首》,而把刊于《新青年》4卷1号“诗”栏目下的九首白话诗,当作最早的“新诗”;不把最早“尝试”和出版个人白话诗集《尝试集》(1920年3月)的胡适看作“新诗”运动的旗手,而将郭沫若视为“五四新诗”旗帜并将他的《女神》(1921年8月),当作“‘五四’以来第一部具有独立特色、影响极为深远的新诗集”[2],就是因为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甚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3]
实际上,“新诗”的“新”意,就是鲜明的时代性。新诗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希望介入现代社会生活,在社会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传统中国社会,诗人的基本出发点是“诗言志”,立足于个人情怀的寄托,虽然也承载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不少作品也有相当的社会性和人民性,但它的社会性与人民性是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立场为前提的,因此,在屈原《离骚》中,是以个人的刚正不阿与怀才不遇,见证封建贵族政治的黑暗;杜甫的“三吏三别”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穷年忧黎元”的典范之作,表现的也是古代读书人有距离的悲悯。而立足于时代转型和社会变革的新诗人,从尝试用“白话”写诗开始,就怀抱着“国语的文学”的梦想,希望通过改造语言去运输新思想,更好地启蒙民众,进行社会动员。
与这种创作立场相一致的,是主题、意象和表现手法发生了重大调整。《新青年》4卷1号“诗”栏目下的白话诗,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直接面对社会问题,敞开“个人”怀抱接纳社会万象,表现上则由主体“自言自语”走向写实、对话和情境描写。沈尹默与胡适的同题诗《人力车夫》和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都有这些特点。像沈尹默的《人力车夫》,虽然开篇还是“日光淡淡,白云悠悠”,延续着传统中国诗人对自然意象的热爱,但它已经是一个背景,随之而来的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街道,将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展现在我们面前:
人力车上人,个个穿棉衣,个个袖手坐,还觉风吹来,身上冷不过。
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坠。
不是抒发个人的进退宠辱和人格趣味,而是要成为时代的神经和时代的歌者,个人激情汇入社会历史的激流,是现代中国诗歌区别于中国古典诗歌最鲜明的特征。郭沫若代表了“五四”时代青春中国的憧憬,展现的是《天狗》《凤凰涅槃》那样破坏旧世界的激情和浴火重生的渴望。艾青与田间代表了内忧外患时代全民族的危机感:“不知明天的车轮 / 要滾上怎样的路程……”一方面,用语言雕刻了苦难中国的形象:“饥馑的大地 / 朝向阴暗的天 / 伸出乞援的 / 颤抖着的两臂” (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另一方面,自觉自愿地把感觉和想象的语言变成了社会动员的语言:“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 敌人用刺刀 / 杀死了我们 /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 ‘看, / 这是奴隶!’”(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这些诗歌从“五四”前后表现社会的不平等开始,一直到当代“朦胧诗”把诗作为争取人的权力的抗辩手段,可以说形成了一种直面社会问题的批判抒情传统。

而与这种传统相对应的,是那些时代色彩极强的憧憬之诗和赞美之诗。早期是对工业化的热情拥抱,比如把工厂的浓烟比喻为时代的牡丹,把摩天塔上的大钟想象为“都会的满月”,把胳膊夹着网球拍子口里哼着英文歌曲的少年,视为现代青年的象征。后来是经由“歌谣化”改造,让诗成为除旧布新的翻身道情,并最终与意识形态联姻,在当代追求“‘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4],并且催生了“政治抒情诗”这样的时代性诗歌类型。而进入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则有人把“淘汰”当作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任何东西都会陈旧的—— / 知识、生命、经验、荣誉……”(《现代化和我们自己》)。
20世纪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大时代,时代的光芒照耀着一代又一代“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的现代中国诗人,感召他们用新的价值、新的视野和境界、新的形式与技巧表现新的生活。诗人歌唱时代生活,有与时俱进的追随,有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介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应该看到现代中国诗人介入时代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理解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逼着加入现代化行程、被侵略者的刀枪逼着站起来救亡图存的民族国家的诗人,在现代性的理解上,在想象风格、语言策略和美学风貌等方面,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诗人。其中一些诗人激情拥抱、追随“德先生”与“赛先生”,将手中的笔当刀枪使用,也是现代性寻求的一种表现形态。毕竟,现代中国诗人既要面对“落后就要挨打”的严峻现实,须要借鉴西方的制度设计与各种观念,又要面对“亡国灭种”被殖民的危机,抵抗外来霸权和文化侵略。这种历史处境决定了现代中国诗人既无法像传统士大夫那样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也不能像西方诗人那样从个人立场出发,表现自我或“为艺术而艺术”。
当然,批判的武器不能替代武器的批判,介入时代的立场不等于有效的介入。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遵循诗歌想象世界的艺术规律。诗无论在辞源中还是理论原典中,都是从心从言的[5],其功能并不是改造世界,而是听从心灵的召唤,通过语言作用于感觉、思维和价值感的改变。因此,人们接受那些直接的、情绪化介入时代生活的诗歌,欣赏他们对传统的批判,对爱情与自由的赞美,对潮流和时尚的追逐,却更认同具有内在介入性的写作,对时尚、表象具有分辨力、洞察力并且具有卓越的命名与表现能力的作品。譬如闻一多丑中垦美的努力,鲁迅对一种言说方式的发明,卞之琳“距离的组织”,艾青对自然意象的社会化改造,冯至以小见大的“沉思”,穆旦“新的抒情”,张枣对生存危机的语言形式转换等。
所谓具有“内在介入性”,一方面当然是能够超越时代的表象,能够把握时代深沉的脉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能够“内在于”诗歌创造的规律。闻一多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五四”时代许多留学回国的诗人,面对现实的乱象,都非常悲哀失望,即使在日本写过体现“五四”精神的《天狗》《凤凰涅槃》等著名诗篇的郭沫若,当他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也是觉得梦的破灭,“满目都是骷髅 / 滿街都是灵柩”,因而反复念叨:“我从梦中惊醒了 / Disilllusion的悲哀哟!”(《上海印象》)。然而,同样面对梦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同样有强烈的幻灭感,闻一多的《发现》面对“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却能追寻和想象更深沉的东西。

闻一多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上海印象》与《发现》的不同,正在于时代性的表面与“内在”。从情感与表现方式而言,《上海印象》似乎更具有“五四”时代的特点,因为它更激越更有批判性,形式上是自由诗,语言是将汉语与英语混合使用,可以说非常时髦。但这些都是表面的,浅层感觉与情绪化的,所以情感虽然激烈却通向感伤消沉。《发现》的不同正在于不是浮光掠影的“印象”,而是基于深厚人文背景的“发现”:虽然现实充满“不是”,但不代表“我的中华”的虚位:那是历史记忆与现实之间的脱节,文化中国与现实中国的错位——因为通过脱节与错位发现“我的中华”就在自己心里,感伤的情绪就得到了心智的反观和想象的疏导。
《发现》的意义不只是心智的运用,同时也是诗歌艺术驯服感情的体现。全诗立足于一个抒情瞬间,聚焦是与不是、在场与虚位的对立,有力体现了主体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诗情的运动跌宕起伏,而节奏的控制更是可圈可点。闻一多曾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创作上可以归入五四浪漫主义谱系,却与当时的浪漫主义诗歌大异其趣,彻底游离了早期“新诗”的滥情主义与感伤主义[6],特别是诗集《死水》,不仅体现了现代中国诗人对时代的独特发现,也以饱满的艺术张力昭彰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可能性和美学魅力。闻一多最可贵的品质是,他知道枪炮与笔墨的两用,做一个民主斗士与做一个诗人的区别。作为斗士,为了社会民主他在广场上振臂直呼,坦然面对反动派的枪口;而在做一个诗人和学者时,他知道必须遵循写诗与做学问的规律,用优秀的作品和学术上的真知卓见,体现现代知识者的自觉:社会良知与艺术(或学术)良知的统一。因此,写诗时,他甘愿“戴着镣铐跳舞”;做学问则用心专一,成了“何妨一下楼主人”。作为诗人,闻一多不仅提出和践行了诗歌“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诗学主张,还通过严格的音节试验,寻找建行建节的规律,为用形式与技巧驾驭感情,避免“新诗”的散文化,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启示。事实上是,像《死水》这样堪称“新诗”界碑的诗篇,其意义远不止抒写了一个时代被压抑的激情,而是为一个时代的激情和压抑,找到了具有辩证法意义的结构与韵律:这是谨严的形式与要求释放的激情矛盾生成的结构与旋律,对象与主体都找到了理想的对应关系。
包括诗人在内,一个现代知识者的良知与自觉,就是在知道自己属于时代与社会的同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能够胜任自己承担的那份工作。诗人之所以是诗人,不是去抢宣传干事的饭碗,也不一定要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以公众代言者自居,而是能够用本民族的语言感觉和想象世界,用语言之光照亮时代现实中晦暗不明和难以言说的部分,为之找到恰当的言说形式和韵律。任何一种即使再强大的力量都无法单独改变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进步需要各种力量形成一种合力,需要山泉溪流般点点滴滴的积聚汇合,需要高度的专业意识和各司其职。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初,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倡导做学问不问有用没用,做好了自然有用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世纪70年代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在法兰西学院发表就职演说,提出知识分子“真正的战斗却在别的地方”[7]的原因。改变世界的同时也需要改变语言,而现代汉语诗歌还很年轻,尚未成熟定型,如何面对传统与西方的双重压力开拓一条新路,成就现代汉语诗歌的光荣与梦想,让汉语在现代化进程中,永远保持活力和美学的可能性,本身就是一个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蔡元培
一百多年来,如前所述,我国诗坛涌现过不少杰出的时代诗人,积累了不少艺术经验,也包括新时期诗歌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和口语风格的实验,上世纪90年代诗歌对矛盾、悖谬感觉的组织和戏谑、反讽等时代美感的探索,以及新世纪诗歌通过地域性反思现代性等,都为诗歌写作的时代性作出了贡献。不过,对时代的理解过于表面,承担时代的方式过于简单,仍然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人总想借助诗歌力量进行社会动员,结果把解放感觉与想象的语言变成了行动的语言;也有人总想借助外力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把需要宁静反观的诗歌写作运动化、时尚化,将诗人的文化身份道德化或政治化,结果赢得了一时热闹却失去了艺术上的千秋。那些惊天动地的口号不过是一阵刮过的大风,任何外贴的新标签也只能吸引眼球而不会给作品加分。而对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理解不够到位,也同样领受到一份需要正视的教训:对“朦胧诗”具有美学反叛意义的“口语诗”,后来在一部分学徒手中变成了“口水诗”,就是一例。
现代中国诗人对时代的担当,不只是道德使命感的问题,也是诗歌能力的问题。或许我们并不缺少担当时代的热情和勇气,需要强调的是对自己工作性质的真正理解,对现代汉语特点的真正掌握,对诗歌想象规律和技艺要求的真正自明。诗歌就是诗歌,诗人就是诗人,诗歌对时代的介入,不只是诗人对自己时代的道德投入,同时是思想和言说能力的考验,而诗歌美学的坚持,也是时代的文化担当。
*本文系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现代中国诗学研究”(项目号:17ZDA12)阶段性成果之一。
[1] 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
[2]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重印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79页。
[3] 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1923年第1 卷第9期。
[4] 贺敬之在《战士的心永远跳动——〈郭小川诗选〉英文本序》中提出:“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按照诗的规律来写和按照人民利益来写相一致。诗人‘自我’跟阶级、跟人民的‘大我’相结合。‘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郭小川诗选续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5] 汉字辞源学相关“诗”字的研究成果认为,“诗”中的“寺”与“志”古音相同,“寺”是“志”的假借。“言”字加入而成“诗”。这与《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构成了对应阐述关系。
[6] 已故诗人陈敬容1940年代在一篇反省写作问题的文章中提出:“中国新诗虽还只有短短一二十年的历史,无形中却已经有了两个传统:就是说,两个极端,一个尽唱的是‘梦呀、玫瑰呀、眼泪呀’,一个尽吼的是‘愤怒呀、热血呀、光明呀’,结果呢,前者走出了人生,后者走出了艺术,把它应有的将人生和艺术综合交错起来的神圣任务,反倒搁置一旁。”(《真诚的声音——略论郑敏、穆旦、杜运燮》,《诗创造》1948年6月第12期。)
[7] 罗兰•巴尔特1977年在《法兰西学院文学符号学讲座就职讲演》中提出:“有些人期待我们知识分子会寻找机会致力于反抗权势,但是我们真正的战斗却在别的地方,这将是反抗各种权势的战斗,而且它不会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斗争。因为如果说权势在社会空间内是多重性的,那么在历史时间中它反过来就是永存的。……权势是一种超社会有机体的寄生物,它和人类的整个历史,而不只是和政治的和历史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在人类长存的历史中,权势于其中寄寓的东西就是语言,或者再准确些说,是语言的必不可少的部分:语言结构(la langue)。”(《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4页。)
作者:王光明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5期(总第44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 袁正领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