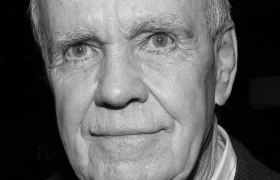在《脱轨的年轻人,脱轨的青春》之后,年轻人系列继续更新。在这个故事里,作为一支乐队主唱的涂俊南似乎更加符合我们对于“年轻”的想象:探索冒险的生活、反抗既定的规范。但是,单读编辑刘婧试图从他身上发掘一些更复杂的面向:矛盾、迷失和落差。在乐队主唱的身份之外,涂俊南也称自己为“写东西的人”和“左翼青年”,这些身份的相容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我们相信,在那些最另类的选择里,往往藏着最普遍的青年心态。
“这歌声就是我们的护身符”
刘婧
1
时间是凌晨 12 点 34 分,台上的涂俊南把最后一件上衣脱掉了。完成这个标志性的动作之后,台下的气氛被推向高潮,躁动迭起。一个顶着鸡冠头的男孩忘我地摇摆晃动,几乎将自己扭成吉他弦,两个女孩突然从对面的吧台冲向舞台近前,疯狂起舞。
这是我第一次走入摇滚乐 live 现场。突如其来的不适感让我本能地向着舞台的反方向挪动,并在一首歌后,彻底脱离了观看演出的人群。我无法放松自己,回忆起上一次见到涂俊南时,他用牛仔外套的下摆擦干电动车坐垫上的雨水,示意我上车的样子。这让我感到舒缓。
此刻他画着浓重的黑色眼线,黑色的牛仔裤和马丁靴上有灰蒙蒙的尘土,耳后和手臂上的文身醒目,金属耳环在灯光下闪动光泽。
今晚是“丢莱卡”乐队的专场演出。上台之前,乐队的五名成员从休息室起身,他们脱掉冬天的厚重外套,将乐器取出,走上不足十平方米的狭促舞台,娴熟地试音、调音,迷幻的灯光打在他们年轻的脸上,大杯的啤酒放在随时可以够到又不会被打翻的位置,同时烟也是不能少的。
整支乐队的舞台风格,因为主唱涂俊南而格外出挑。涂俊南极其擅长调动全场气氛,他会在每首歌前做简短的介绍,即兴开上一两句玩笑;灵活地配加喇叭、铃鼓,以增强现场效果;在演唱中忘情地跳跃、摇摆,任性地抽烟、喝酒,宛若一个派对的主人;除此,他还有个人符号性的物件:一顶列车乘务员的帽子。他用黑色胶带遮住了乘务员的帽徽,配上了前苏联共产党党徽。他很喜欢这种来自前苏联的“硬美学”,并由此设计了乐队两次巡演的海报。

Temple Bar & Live house(作者拍摄)
这个 live house & 酒吧位于鼓楼东大街的一个院内,热爱夜生活和青年文化的年轻人大可能轻车熟路地找到它。然而我像一个笨拙的闯入者,在地图的指示下,仍三次错过它的大门。在遍地的烟头中间,化着浓妆、发色各异的年轻人三五成群地聊天、嬉笑。我站在角落里,看着墙上意义不明的巨幅涂鸦,从房间内传出的音乐声,像是被闷在被子里的呼号。
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青年亚文化以各种符号彰显独特性,将自我与他者区分。我自认是青年文化的他者,对这种文化/生活方式怀有复杂的情绪。14 岁那年,第一次读到《麦田里的守望者》时,我因男主人公霍尔顿的装腔作势感到可笑,也对他不顾一切地离家出走羡慕不已。十年后,我仍然在一种旁观者的嘲笑和惊羡之间摇摆,这一摇摆贯穿了我与涂俊南的每一次对话。
2017 年 6 月,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涂俊南开始全职经营这支从大学里搞起来的摇滚乐队。除了摇滚主唱这重身份,涂俊南身上的其他重要标签还包括“写东西的人”和“左翼青年”。
初次见面,我们在一个位于五道口的青年社区简短聊了几句。当天,他是“失败青年”沙龙的圆桌嘉宾,甫一出现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涂俊南的身上有股强大的主唱气场,自信、不羁,同时又亲和、有条理,在严肃和调侃之间游刃有余,这让他所呈现的一切都极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分享会上,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没有工作且没有稳定收入、从江西来到北京的大学毕业生”:中文系毕业、从小想当作家,但至今没有令自己满意的作品、没有任何发表;作为一支当代摇滚乐队的主唱,不识谱、不会乐器;身为儿子,没有像身边人一样工作、考研或者出国,给父母一个交代。

“失败青年”分享会上的标语(作者拍摄)
直到一周之后,我们坐在他的出租屋里长谈时,我才意识到,他远没有我所预想的那样焦虑茫然、难以自洽,我为他所呈现的、我至今找寻不到的自足,感到惊讶。“年轻人”这个标签在他的身上异常醒目,他无疑是我们这代青年中的某种典型。
2
涂俊南住在雍和宫大街旁的北新胡同深处。2017 年 3 月,同样搞音乐的师哥租约到期,便将房东介绍给了他,他续租了这间屋子,每月房租 1600 块。在寸土寸金的北京二环内,这个房租已算相当价廉。
那一年,我在离这儿不远的一家出版社实习。下班后,我会沿着雍和宫大街,一直走到东四北大街,目光扫过两旁的藏传佛教用品店,心中为自己毕业后的工作做盘算。而当时的涂俊南已经下定决心:绝不过上班打卡的生活。
采访当天,北京的天空飘着细雨,彼时的愁绪如头顶灰暗的乌云。涂俊南骑着电动车出现。他经常骑着电动车穿过北京的大街小巷,歌曲旋律大多是在车上哼出来的。上一个电动车的电瓶在几个月前失窃后,如今就停靠在他家人来人往的门前,坐垫的皮套破败得不成样子,空荡的车肚成了快递寄放处。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从里面取出曹征路的《问苍茫》,对这种方式的可行性感到信服。
这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呈长条形,如一条色彩缤纷的隧道。除了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厨房、客厅、书房和卧室同处一个空间,没有功能区的分隔,但也温馨、妥当,充满了涂俊南浓烈的个人气息。
搬进来没多久,他就将屋顶的日光灯拆掉,沿天花板边缘安装了 LED 灯带;房间的尽头是一张大床,床后的墙体被巨幅喷绘覆盖,那是乐队 2017 年 5 月在学校大礼堂举办的专场演出宣传海报;正中央的中国地图用于定巡演地点,云南省的下面被他标上了 Bob Dylan,因为“云南省长得像 Bob Dylan”;韩国光州事件图册、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海报、Joy Division 乐队和 David Bowie 的海报、乐队成员合影、乐队巡演海报……就好像他把自己的各类喜好展开,铺满了整间小屋的墙壁。
那天,他的床头放着最爱的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诗集《未知大学》和短篇小说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他为作家创作的歌曲《燃烧的平原》,是乐队每场的必演曲目。书桌上方的墙壁上贴着几张照片,一张父母的合影,还有一张女友胡晋溢做出可爱鬼脸的大头照。

罗贝托·波拉尼奥,智利诗人和小说家。
胡晋溢已经不像之前那样焦虑男友的生活状态了。两人自大一暑假确立恋爱关系,至今已有四年多的时间,在无数的争吵、磨合之后,终于达到外人无法体会的理解和妥协。尽管她还是时常就“不要浪费时间”这件事,与涂俊南展开拉锯战。
“他经常睡到下午一两点才起床,虽然晚上睡得很晚,但是这一天基本就荒废掉了。所以我会为这种事说他,但也不能总说,因为他会烦”,“不过他这段时间好点了”,她补充道。她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劝导”起了一点作用,但她还是不能完全理解,成天把“写东西”挂在嘴边的男友,为什么忙着乐队、忙着社交,忙着一切与写作无关的事情。涂俊南的说法是,“我很难跟一个不写东西的人解释我现在的状态为什么没法写东西”。
唯一肯定的是,搞乐队确实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面对两者之间的矛盾,涂俊南显得有些焦虑。“管理好一支乐队需要应对和处理的繁琐事务,并不比打卡上班轻松。”而且,这几乎是个毫无利润可言的行当。对于男友没有稳定收入和工作这件事,胡晋溢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我自己活得这么茫然,他好歹有个明确的方向,只是不赚钱而已。”
在进入现在这家文化公司做视频编导之前,胡晋溢在多个地方实习过,仔细比较、思考后,她觉得视频剪辑除了技术层面的技巧,更关乎内容本身的质量,她更想做一个内容生产者。彼时,原本对实习表现过兴趣的涂俊南转而投身乐队事务,并且越来越投入。母亲时常会在与女儿的通话中问起涂俊南的状况,“那个小涂怎么样了,还没找工作呢?”
两人可以维持目前的生活,一个原因是胡晋溢每月的收入足以负担自己的开支。在涂俊南手头紧张的时候,她还可以在吃饭、看电影这样的约会项目上买单。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涂俊南的房租长时间由父母支付。“这是我每个月都要经历一次的屈辱”,涂俊南告诉我,自己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心安理得了,也会有一些来源不定的收入,比如微信文章的打赏,参演朋友的片子获得的酬劳。“现在每个月零零散散的收入也有……两三千吧”,他思索着说。
收到钱的那一天,涂俊南会给父亲发去微信,“谢谢爸”。除此之外,父子俩没有更多的话可说。胡晋溢几乎从未直接见过涂俊南与父母交流,他们的相处状况大多来自涂俊南的转述。有一次,涂俊南告诉她,他因为生活费在电话里跟母亲吵了一架。根本问题不在于钱,而在于母亲对儿子现状的忧心。
采访结束几个月后,我看到涂俊南和胡晋溢的朋友圈里频繁出现了一家酒吧的信息。发稿前几日,涂俊南给我发来消息,告诉我他在东四开了一个酒馆,酒馆及其他方面的收入让他的经济状况好转了不少,现在的房租都是自己支付了。他希望我补充上这个“好消息”,“这半年多以来还是发生了不少变化,不想让父母和其他关心我的人为我担心。”
在形容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时,涂俊南用的词是:不熟。“我们之间不是修复关系,而是先得增加了解。”这种彼此之间的陌生感由来已久,始终无法得到改善。
小时候,体弱多病的涂俊南经常请病假在家,繁忙的父母很少出现在他这些独处的时光里。作为南昌市最优秀的高中生物老师之一,涂俊南的母亲惯于强硬的管教手段;10 岁那年,因为父亲的工作出现了一些意外的变故,家境陷入漫长的低迷。长久地,陪伴涂俊南的是小男孩旺盛的“破坏欲”,和大量母亲买回家的书籍。他从一次次规模微小的破坏行为里收获乐趣,也从郑渊洁的儿童读物里获得有关是非黑白、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
进入高中后,他曾有一段时间寄住在离学校更近的大伯家,他至今怀念那段时光,“那里没有天然的、无可辩驳的权力压制。我喜欢朋友关系胜于亲情关系,因为它是基于纯粹的人的状态”,其结果是,“我对亲情没有什么信任。”
如今,父母主要通过涂俊南发布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的公开信息,以及发布这些信息的时间,来获知儿子的近况。偶尔,涂俊南会收到母亲的微信:“怎么这么晚睡?”“怎么又文身了?”“生病啦?”她对涂俊南的知情力,与他的 7464 个微博粉丝基本相同。
在关于父母的话题上,我们的对话总是进行得非常艰难,他长时间的沉默让我感到不安。但是我觉得,他在这些时刻所呈现的矛盾、回避、犹豫,才是一种更普遍、更真实的青年状态。
3
在那些父母没有留意的成长岁月里,涂俊南强壮起来,不论是身体还是心智。
初中毕业那年,学校出台新政策以阻止优秀毕业生流失到其他高中,并在初三上半学期安排重新分班。为了反对这个举措,涂俊南发起了一场抵制运动。“一天放学之后,我在每个班的黑板上写了一些号召大家抵抗的话,还留下了自己的名字。”言论造势进行得异常顺利,之后的好几天,涂俊南继续前往每个班级“煽动”,并实名给校长写了一封信,意思简明:我们学生都不同意,所以你不能这么干。
后来,新政策不了了之,这场小动乱以学生的大获成功告终。
进入高中后,涂俊南寄住在大伯家,彻底挣脱了父母的束缚。他担任学生会主席和多个协会的会长,逃课,办活动,带同学玩,晚上漫步江边谈恋爱。在这所南昌最好的高中里,他挥霍着自由,巩固着自己对是非黑白的理解和对权威的无视。直到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这种生活的难得,“我以为大家都这样,后来发现并不是。”
现在回想起来,在这条反叛之路上,涂俊南没有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唯有高二升高三那年的暑假,一直被他“挑战和得罪”的政治老师,将他调离了“重点班”。“我记得他的脸上是一种得意的表情,我觉得自己‘被打败了’”。
为了扳回这一局,涂俊南开始每天 6 点起床,一直学习到晚上 12 点,他疯狂地借笔记、做试卷,查缺补漏,两个月后,每次考试徘徊在一百名左右的他一下子进入了年级前十。那天,他带着胜利者的姿态,重回“重点班”。在几个月后的高考中,他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提前批次录取。
自那之后,更广阔的自由才真正降临。涂俊南终于顺利地离开家,离开南昌,前往北京,那里聚集着他从网络上看来的、令他心向往之的一切:音乐、艺术、思想。

涂俊南所开的暂停酒馆
在一篇自述里,他这样描述中学时期的自己:组织学生活动、热心破坏校规、365天谈恋爱不间断、最后凭小聪明和笨功夫过考试的搞文学的小混混。
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大学里,他做中心人物的意愿没有减弱,但似乎一直没有用武之地。胡晋溢记得,为了帮助男友竞选学生会主席,她曾熬夜帮他制作演讲的 PPT。那期间,涂俊南几乎玩遍了中国,还去了日本、朝鲜和俄罗斯。但是大部分时候,他只是在一种混沌不清的生活中。“每天都在瞎玩、瞎混,整晚整晚地不睡觉,跟朋友或者不认识的人看演出、喝酒,独自征服一个又一个天台,假装自己是城市里孤独的拿破仑。”
直到大三,一个突然的转机出现。涂俊南是大学吉他协会的成员,吉协在鼎盛时期是学校一支很有影响力的团体,在他们的大本营—— 108 排练室里,乐器、音效以及其他娱乐工具一应俱全,除此之外,还有床位。涂俊南大三那年,这个用了将近十年的基地被勒令停用,吉他协会里“厉害的前辈”也都纷纷毕业离开,在这个青黄不接、危机重重的阶段,涂俊南站了出来。这正是他发光的时刻。
常年的四处晃荡有了回报。他偶然发现了一处还未被使用的行政楼,于是跟李堂华——比他小两届的师弟、现在“丢莱卡”的吉他手商量,用其中一间最靠边的屋子 5052 排练。很快,涂俊南在网上买了一张行军床,当年 5 月份住了进去,一住就是半年。后来,一个回老家的朋友把自己的电风扇、电饭煲、沙发床贡献了出来,他们又去各个宿舍楼收了二三十个床垫。5052 教室不仅是乐队的排练室,而几乎变成了一个青年旅馆。
5052 ,是“丢莱卡”乐队的起点,也是涂俊南的新坐标。在这里,他用三四天的时间,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盲虎》。尽管如今乐队不再演出这支曲目,但是当时,它给涂俊南带来的喜悦无以复加,“觉得自己太厉害了,这歌太好听了!”歌曲的三段歌词分别写的是人的童年、青年和中年,“都是盲目的,什么都看不清,一生就过去了”,涂俊南这样解释他的创作。这首歌多少表露了他当时的心境。“我记得,在那个排练室里,我还往墙上撞过,觉得自己很差劲,想实现的东西无法实现。”
不过,有了新的据点,有了处境相似的朋友和创作的满足感,生活的主线慢慢出来了。“做乐队这件事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必须要几个人共同协作,一起创作加上一起演出。所有人共享一种喜悦,让人觉得没有那么孤独。这种感觉太美了,直到现在我也没找到其他能给我类似感觉的事情。”
2017 年 3 月底,乐队正式定名为“丢莱卡”,乐队成员也基本固定下来。这期间,涂俊南通过各种渠道联系 live house,演出,参赛,“丢莱卡”的名字渐渐为人所知。那一年的 5 月 23 日,乐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大礼堂举办了自己的专场演出。“那是我们的第九场正式演出,竟然就做专场。很不成熟,自己的歌只有四五首,剩下的都是翻唱。”当天,八百人的礼堂只坐了二百来人,但是涂俊南回忆,场下的观众很买账,一直跟着音乐嗨。

“丢莱卡”首张 EP《健忘的平原》
在乐队演出的初期,胡晋溢每一场都会到现场捧场。见证“丢莱卡”一路的变化,胡晋溢觉得他们的变化很大,不论是歌曲的完成度,还是涂俊南的舞台风格。他们逐渐从周中演出的冷门乐队,成长为周末演出的热门小咖。
2017 年 11 月,“丢莱卡”被北京 school award 评为年度最佳一年级乐队。来年 1 月,首场巡演“思念宇宙”从北京一路向南,直达广州。半年之后,他们又完成了第二场巡演“健忘的平原”。出完专辑再巡演,这是音乐圈的规则,但涂俊南就是要打破它。
从学生生活到舞台经验,他所讲述的一切,对于我这个循规蹈矩、经历贫乏的人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它们让我得以理解他所渴求的刺激与满足,以及那种无法撼动的自信。
……
本文系节选,